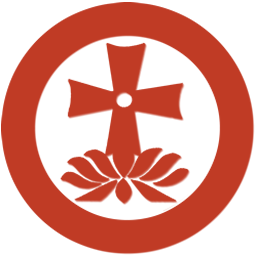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1年第17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137
陈才俊(暨南大学)
摘要:1883至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完成自己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此期,正值其17至26岁,乃其知识积累与思想形成之重要阶段。孙中山因仰慕西方现代文明与科学技术而在香港皈依基督教会,因谙熟基督宗教乃西方文明之根而于大学时代潜心研习西学,因认同西方君主立宪制度而萌生革新中国旧制的思想。此为其早期思想形成之基本理路。孙中山早期思想的核心并非武装革命,而是救国济民,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具体手段则是“改良”与“革新”。
关键词:孙中山、基督宗教、革新救国、现代化
DOI: 10.29635/JRCC.202112_(17).0004
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1866—1925)从香港西医书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毕业。此时,距其1883年秋入读香港拔萃书室(Dioceson Home,Hong Kong)已近九载。此间,他除赴檀香山短期省亲和在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创办之附属医校习医一年,其余时间均在香港求学。孙中山之所以选择在香港完成自己的中、高等教育,虽由多种因素促成,但根本缘由在于香港的西式学校有别于中国传统学塾,主授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有助于其开拓视野,增长才智。1883至1892年,正值孙中山17至26岁,乃其知识积累与思想形成之重要阶段。抵达香港不久,早已倾心耶稣之道的孙中山即皈依基督,求学期间所接触者亦多为教会中人,故其早期思想深受基督宗教核心价值影响。[[1]]
孙中山曾谓:“从前人人问我,你在何处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云:革命思想系从香港得来。”[[2]] 他还称在香港西医书院,“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3]] 其香港西医书院同学兼好友关景良(1869—1945)亦言:“至一八八九年,总理的言论已充满革命思想,要推翻清廷,废除帝制。”[[4]] 但审视孙中山香港求学期间之生活轨迹不难发现,其因仰慕西方现代文明与科学技术而皈依基督教会,因谙熟基督宗教乃西方文明之根而研习西学,因认同西方君主立宪制度而萌生革新救国思想。 严格意义而言,孙中山香港求学时代之所谓“革命思想”,尚未具备真正“革命”之意,只是其“改良祖国”之“革新”主张。而他本人及同侪称其当时倡言革命,“都不过是拔高过往事迹的溢美之辞”。[[5]] 可以说,孙中山“首先是一个深受现代西方文明熏染之基督徒,然后才是一名悬壶济世之现代医师,进而成为一位从事‘医国事业’之伟大改革家”;“‘革命’一词不足以涵盖孙中山终身服膺与践行之‘救国济民’宏志,而仅为其一端”。[[6]]
一、因仰慕西技而皈依基督
孙中山对基督宗教产生兴趣始自檀香山。1879年5月21日,他随母亲从澳门出发,乘英国火轮船“格兰诺去”号(S. S. Grannock)前往檀岛投靠兄长孙眉(1854—1915)。在火轮船上,他惊叹“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7]]。此其所言之“西学”,更多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即“西技”。孙中山在檀香山英美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之后渐趋明白,其所乘火轮船之船长和船员皆为基督徒,船之铁梁、机器等均由基督徒发明与制造;其所耳濡目染、置身其中之西方建筑、音乐、礼仪,西人之世界观、生活方式乃至行为举止,无不深受基督宗教之影响。
1879年9月,孙中山进入檀香山英国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亦译“英国国教会”)创办之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College)念高小三年,其后至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即
即即“美国公理会差会”,简称“美部会”)创办之奥阿厚书院(Oahu College)念初中半年。在檀岛读书期间,孙中山因参加学校教堂举行的早经晚课,诵读《圣经》经文,渐谙基督教义,遂对基督宗教产生浓厚兴趣,并表达领洗意愿。然而,其兄孙眉“因其切慕耶稣之道”,即“着令回华”[[8]]。檀香山的学习经历在青年孙中山心中点燃两个火种:一是“对基督(宗)教高度的热情”,二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9]] 及至孙中山到香港求学,这两个火种在其心中愈燃愈烈,最终形成一股革新救国的合力。
1883年秋,孙中山入读英国圣公会在香港创办之拔萃书室,正式开启在港求学生涯。 翌年4月15日,他转学至香港中央书院(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10]] 。在香港,由于没有兄长孙眉的约束,孙中山“每星期日恒至邻近道济会堂听王煜初牧师说教”[[11]],且广泛密切接触中西教会人士,不仅逐渐对基督宗教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且皈依基督的愿望愈益强烈。孙中山初到香港时,曾寄宿于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传教士喜嘉理(Charles Robert Hager,1851—1917)牧师位于拔萃书室附近之临时传教所。他们同吃同住,很长时间生活在一起。喜嘉理1883年3月31日抵港,一直不畏疲劳,不惧艰辛,全心全意把自己奉献给“中华归主”(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的传教事业。孙中山对喜嘉理刻苦耐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感佩有加,心生敬意,更坚定其领洗皈依的决心。[[12]]
据喜嘉理对孙中山的忆述:“一八八三年秋冬之交,余与先生初次谋面,声容笑貌,宛然一十七八岁之学生,……余职在布道,与之觌晤未久,即以是否崇信基督相质问。先生答云,基督之道,余固深信,特尚未列名教会耳。余询其故。则曰,待时耳,在己固无不可也。”[[13]] 由上可知,喜嘉理认识孙中山不久,即询问其是否崇信耶稣基督。孙中山明确表示自己深信基督之道,且随时随地愿意领洗。1884年5月4日,由喜嘉理施洗,孙中山正式皈依基督教会,取名“日新”。“日新”二字,盖取《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喜嘉理1912年忆及此事,仍对孙中山领洗入教之决定大为赞赏:“夫居今日宗教自由之世,而言皈依基督,固不足奇;当日情势,与今迥异。明认基督教者,殊不多觏。盖明认基督者,人咸耻与为伍。以故人人咸有戒心。然先生热心毅力,竟能化导其友,使不得不出于信仰之途,其魄力之宏,感人之深,可略见其端倪矣。”[[14]] 孙中山皈依教会乃其切身感悟和认真思考之后的选择,所以毅然决然,至诚恳切。
孙中山领洗不久,便于当年夏天协助喜嘉理在香港、澳门及珠江河畔等地传教,分售《圣经》及宣传单张,并劝说友人入教。正因为他对基督教义的宣传和解释,其翠亨幼时伙伴陆皓东(1868—1895)才向喜嘉理表达对耶稣基督的敬仰之心。[[15]] 同样也是因为他的介绍和鼓励,其香山同乡、同时也是檀岛同窗唐雄(1865—1958)才鼓足勇气请喜嘉理施洗入教。喜嘉理言:“先生既束身信道,即热心为基督作证,未几,其友二人,为所感动,亦虚心奉教。”[[16]] 此二人即陆皓东和唐雄。
孙中山中学毕业时曾有一个愿望,即成为传教士。所以,他的最初选择是入读神学院,期冀日后献身传教事业,但由于其时香港及附近没有完善的神学院,故只能放弃。喜嘉理曾感叹:“盖彼时其传道之志,固甚坚决也。向使当日香港或附近之地,设有完善之神学院,俾得入院授以相当之课程,更有人出资为之补助,则孙中山先生者,殆必为当代著名之宣教师矣。”[[17]] 入读神学院的梦想破灭后,孙中山亦有意学习军事或者法律,然皆因中国其时尚无此类学校而作罢。但同时他发现,新教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医学,其性质本来就包含基督宗教“救人”之精神。在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和华人基督徒看来,医疗工作是传教以外最能接近基督信仰的媒介。孙中山认识到“医亦救人苦难术”[[18]],遂选择学习西方医学,并于1887年10月至1892年7月就读于英国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香港创办之西医书院。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期间,所接触的中外人士多为基督徒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是西方来华传教士,另一部分则为深受西方文化濡染的道济会堂(To Tsai Church)华人教友。道济会堂原为英国伦敦传教会在香港创立之华人聚会团体,后由华人牧师王煜初(1843—1902)自设会堂,1886年成为香港首个华人自立教会。伴随对基督宗教的理解愈来愈深,孙中山渐趋认识到,基督宗教乃西方文明之根、西学之源。在年轻的孙中山看来,基督宗教就是现代化的标志。
当然,孙中山最初对基督宗教之仰慕,还不完全出自宗教信仰之故,而是如其所言,乃“慕西学之心”[[19]]。中国早期革命家冯自由(1882—1958)曾言:“考总理之信教,完全出于基督救世之宗旨,然其所信奉之教义,为进步的及革新的,与世俗之墨守旧章思想陈腐者迥然不同。”[[20]] 此可谓对孙中山因仰慕西方现代文明与科学技术而皈依基督教会之最好诠释。
二、因倾心耶教而探究西学
孙中山领洗皈依耶稣基督之时,无疑对基督宗教充满极高热情,但他的这种热情并非纯粹发端于宗教信仰本身,而是来自于基督宗教所产生之实用效果。他深切感悟到,基督宗教能够与时俱进,不断自我更新,以满足人类对现代化如饥似渴之需求;而反观中国之儒教、佛教和道教,它们均往后看而非向前看,捆绑中国两千余年,导致国家固步自封,裹足不前。[[21]] 孙中山通过对中西宗教理念之深刻比较,愈发认识到只有基督宗教所产生之实用价值(而不纯粹是其宗教信仰),才是催生中国现代化之重要手段。
孙中山在香港求学期间,随着对西方文化的不断熟悉,渐趋认识到基督宗教乃西方文明之核心价值,西方的现代化亦完全有赖于基督宗教文明之与时俱进。他深刻意识到,要想更好地服务中国社会,就要让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而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则必须唤醒尚在沉睡中的广大民众。但是,中国若想重构自己的现代文明,选择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呢?孙中山觉得,基督宗教是不错的选择,已被西方社会证明具有切实可行性。但他也明白,基督宗教是伴随西方殖民势力而强行进入近代中国的“洋教”,广受国人排拒和诟病,其时尚无法为国人所接纳。故此,他决意学习西方现代文明与实用知识,以实现自己救国济民之宏志。对孙中山而言,其时最切实可行的救国理想,是学习西方传入中国的现代医学,帮助国人战胜疾病,保障国民身体健康,实现国家富强之梦。
基督宗教“是一个‘入世型’或‘救世型’宗教”,从创立之始就有强烈的入世情结,“有对人类福祉、尘世生活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关怀”[[22]],并对现世抱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基督徒不可“忽视对他人的道德关怀和社会责任,因为真正得蒙上帝喜悦的人不仅需保持灵魂的圣洁和信仰,而且应以《圣经》中救死扶伤的耶稣为表率,在尘世生活中积极促进他人的福利和社会的公义”。[[23]] 作为基督徒的孙中山,深谙基督宗教入世之道,明白服务社会应尽之责。他选择学习西方医学,以期成为一名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医生,实乃以基督徒救国济民的“入世”之道,转化为以医术救人的“济世”之途。自《国语·晋语》言“上医医国,其次疾人”以降,中国古今不乏“上医”走上“医国”之路,然无人能出孙中山之右。孙中山乃中国当之无愧“上医医国”第一人。
英国伦敦传教会在香港创办之西医书院不仅是香港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而且是中国近代医学高等教育的发端。该校将近代西方高等教育思想作为办学的基本理念与准则,其组织机构、课程设置、考试方法等均移植于当时欧洲的大学;其师资队伍高度英国化,且广纳西方社会精英从事一线教学工作。[[24]] 书院主要创办发起人康德黎(James Cantlie,1851—1926)在第一届毕业生典礼上指出:“书院所研习的课程,其依据可说与不列颠各医科学校所编定者相似。”所以,书院的课程“自始以五年的编制为目标”,且均以英文授课。[[25]] 从香港西医书院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其教授的课程均为西方现代科学之前沿,代表当时世界科技的先进水平。故罗香林(1906—1978)言,“是西医书院之创立,不特与香港教育之进程有关,抑亦与中西文化交流之进程有关也。”[[26]]
孙中山甫进入香港西医书院,便如饥似渴地研习与探究西方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据关景良忆述:“总理在院习医科五年,专心致意于学业,勤恳非常。彼于日间习读医学,夜则研究中文,时见其中夜起床燃灯诵读。”[[27]] 香港西医书院创立之时,正值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学说风靡欧美,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之风亦正盛。当时,孙中山“最爱读之书乃《法国革命史》(蓝皮译本)及达尔文之进化论”,“后乃知其思想受此二书之影响不少也”。[[28]] 达尔文是著名英国生物学家。其通过环球实地考察之后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彻底颠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尤其冲击基督宗教的上帝创世论。孙中山研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e)及法国历史学家米涅(François A. Mignet)的《法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1789 to 1814)时,尚无中文译本。可以说,“国父之研究此类繁著,非第探索繁颐,且在中国亦开风气之先焉。”[[29]] 另据康德黎回忆,孙中山还“研究国际法、军事战术、海军建设、各种财政、治国方略及各种流派的政治学”。[[30]] 总而言之,孙中山在西医书院读书时,对西学的涉猎非常广泛。
1890年,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的孙中山,曾上书香山乡贤、李鸿章(1823—1901)重要幕僚郑藻如(1827—1894)。其自谓:“某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31]] 24岁的孙中山如果对西学不是相当熟悉,不可能在63岁的郑藻如面前如此自信。1894年6月,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近两年的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亦自述:“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泰西农学之书间尝观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32]] 此亦为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期间广涉西学的又一明证。
孙中山孜孜不倦地探究西学,是希望利用所学知识服务国人,期冀中国步入现代化之途。“盖欲合其学术之研究与实际生活,及救国意志为一体,即古所谓‘寝馈无忘’也。”[[33]] 其1890年的上郑藻如书,已尝试对封建中国“农桑之不振”“鸦片之为害”“天下之失教” 三大问题予以剖析,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他指出,“之斯三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将见一倡百和,利以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吾国之大幸也。”[[34]] 孙中山1891年前后所撰的《农功》一文,更是对以西方学术兴中国农政有较深入的阐论。他首先阐释世界各国农政的先进之处,然后分析中国传统农耕思想的沉疴痼疾,最后提出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建设性构想。他理想的现代中国是“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并认为此乃“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35]]
在香港求学期间,孙中山接触最多的无疑是教会人士。当时与其有共同语言且深受西学影响者,绝大部分为奉公守法的基督徒。他也寄希望于这些基督徒通过借助西学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1891年3月27日,孙中山与同人在香港创立基督徒团体“教友少年会”。他以 “孙日新”之名在上海广学会《中西教会报》发表之《教友少年会纪事》言:“辛卯之春,二月十八日,同人创少年会于香港,颜其处曰‘培道书室’。中设图书、玩器、讲席、琴台,为公暇茶余谈道论文之地;又复延集西友于晚间在此讲授专门之学。”[[36]] 此“西友”所 授“专门之学”,即西学。孙中山等人创办教友少年会,一方面“以联络教中子弟,使毋荒其道心,免渐堕乎流俗,而措吾教于磐石之固也”;另一方面“集俊秀于一室,交游尽属淳良,备琴书于座右,器玩都成雅艺”。[[37]] 教友少年会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在全国形成一种倡导西学的风气,并藉此为革新社会营造气势。《教友少年会纪事》乃迄今所见孙中山首次署名公开发表的文章,彰显青年孙中山崇尚西学之志。
随着孙中山在香港获得的西学知识愈来愈多,其与耶稣基督的距离也就渐行渐远。尤其是研究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后,他便“雅癖达文之道(Darwinism)”[[38]],“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39]]。可以说,孙中山因为倾心基督宗教的与时俱进而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但在对西方文明的深入探究中又超越信仰的局限性,深度发掘宗教的实用性。
三、因认同西制而谋求革新
基督宗教的入世思想体现于,耶稣基督从天国降临人间,来到寻常百姓之家,指引受苦受难的众生迈向永恒幸福的天国,不但不主张远离尘世、无欲无求,而且十分关注世俗之人的各种权利;基督宗教高度重视人权,鼓励人们谋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基督徒具有承担人类苦难和社会义务的责任感,主张尽心尽力服务社会。按照传统基督教义,基督福音要证实其为“天国之音”,也必须首先为“社会福音”,体现出其社会拯救之义。孙中山抵达香港不久即皈依耶稣基督,接受基督宗教承担人类苦难和投身社会拯救的理念,所以自然而然培育出救国济民的博大情怀。
孙中山赴港求学未几便发现,香港与香山仅50英里之遥,但两地情形却有如天壤之别。据其回忆:“在香港读书,工课完毕,每出外游行,见得本港卫生与风俗无一不好”;而回到香山,“因在乡间要做警察及看更人,方可斯二者有枪械在手,晚上无时不要预备枪械,以为防卫之用”。[[40]] 在家乡翠亨,他目睹社会充满危险扰攘,百姓生活提心吊胆。令孙中山大为不解的是,何以英国人在短短数十年间就能将香港建设成如此先进的地方,而拥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却做不到?后来他渐趋意识到,二者的差距归根结蒂源于社会制度及政府治理之差异。“香港腐败事尚少,而中国内地之腐败竟习以为常,牢不可破。”他最初以为仅香山一地腐败盛行,而事实却是,“及后再到省城,其腐败更加一等,由此想到中国之官势位愈高,贪污愈炽,所有北京各处更有甚矣”。[[41]] 可见,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是阻遏中国社会进步和影响民众生活幸福的首要障碍。孙中山曾与香港的英国友人议及此事,得到的答案是:“良好之政府并非生生俱来,须人事造成之。数百年前英国官员多系腐败,迨后人心一振,良好政府遂得以产出。”于是,他“深知如中国无良好政府,办事必不能成”。[[42]] 随着在香港学习时间的推移以及对西方社会制度认识的加深,孙中山“继思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亦然”。他知道,“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不良之政府为之”[[43]]。他最终明白, 中国只有革新政治制度,改良政府治理,方能开启现代化进程。
早在檀香山求学之时,孙中山看到中西社会发展及教育水平的差异,便“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且“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其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44]] 求学香港期间,孙中山在广泛研习西方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的同时,亦对西方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有一定的思考。尤其是他就读的西医书院,学校的管理人员及任课教师多为具有英国背景的社会精英与学术翘楚,有些还是享誉国际的学者;学校的管理体系与运作模式亦完全英国化。孙中山通过学校的知识积累以及自己的切身感悟,愈来愈觉得革新清朝专制统治的迫切性。
香港西医书院有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对青年孙中山影响甚巨。一位是来自苏格兰的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康德黎,另一位是从英国学成归来的香港人何启(Ho Kai,1859—1914)。此二人均具有英国伦敦传教会背景。他们倡导的君主立宪维新主张,直接影响到孙中山早期思想的形成。
康德黎1887年6月抵达香港,在雅丽氏利济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行医,并参与倡议创办香港西医书院。作为西医书院的主要创办人及第二任教务长(1889—1896年在任),他对该校的早期发展贡献卓著。康德黎不仅是“第一位为孙中山上课的老师”,而且是“孙中山崇拜的偶像”[[45]]。他具体讲授的课程为解剖学。康德黎对孙中山的才智颇为欣赏,在其入学半年后即随带出诊,结识在港的英国要人,后来还携其到广州麻疯病村做医学调查。在西医书院第一届毕业典礼宴会上,康德黎特意安排孙中山代表毕业生致词。孙中山在与康德黎的密切接触中,不仅掌握了精湛的医疗技术,而且了解到西方的民主法治精神,激发其救国济民的宏大志向。“迨毕业而后,在社会上行走,遂毅然决然脱离医学,而转以救国为前提。”[[46]] 康德黎亦“极希望中国现代化,并衷心支持孙中山要促使中国现代化的决心”。[[47]] 不过其时的康德黎,“以其维护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立场,努力说服正在求学的孙中山放弃更为激进的共和政见”[[48]]。据康德黎回忆,他们夫妇曾有几次劝说孙中山接受君主立宪革新方案的长谈。[[49]]
何启13岁赴英国留学,先后获得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和大律师资格,回到香港后创办雅丽氏利济医院,参与倡办西医书院并教授法医学。何启“可能是孙中山接触到的企图按照西方的路线使中国现代化的人们中的第一人”[[50]]。1887年2月16日,何启在香港英文《德臣西报》(China Mail)发表《中国之睡与醒——与曾侯商榷》(“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a Reply to Marquis Tseng)[[51]] 一文,反驳清廷原驻英、法、俄等国公使曾纪泽(1837—1890)在伦敦《亚洲季刊评论》(Asiatic Quarterly Review)发表的《中国先睡后醒论》(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52]] 一文暴露的清朝官员陶醉于洋务运动成就而不思政治体制改革的陈旧观点。曾纪泽宣称中国经过练兵制械的洋务运动,已经从先前的睡梦中觉醒,只要沿着军事近代化的国策继续发展,将成为稳固的国家。何启则历数清廷官吏沉迷于洋务运动局部改革而引发的种种弊端,指出中国其实仍然昏睡在君主专制的政治困局之中。他指出:“今者中国,政则有私而无公也,令则有偏而无平也。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啻如奴贱也。官吏如虎,而君上纵之不啻如鹰犬也。”进而,他提出“君民共主”的主张:“民之于君为更贵。以有民,不患其无君。而有君,独患其无民也。此以见民之于君为尤先。以有民,然后可有君。无君,必先以无民也。”“国之所以自立者,非君之能自立也,民立之也。国之所以能兴者,非君之能自兴也,民兴之也。然则为君者,其职在于保民,使民为之立国也。其事在于利民,使民为之兴国也。”何启强调,若欲振兴国势,必须内政改革;若要促成君民同心,就要变法维新,公平治国。只有这样,中国的觉醒才有出路,否则就是请来古代圣贤执政,亦难得民心。而要改革,则需:“国有公平,然后得民信;先得民信,然后得民心;先得民心,然后得民力;先得民力,然后可以养民和;可以养民和,然后可以平外患。”“君民相继,上下一德,更张丕变,咸与维新,庶可有益于民生。”[[53]]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聆听何启授课之余,自然了解其倡议中国进行君主立宪改革的主张。特别是在孙中山大学三年级时,何启被港督任命为立法局议员,在香港社会影响颇巨,并引发青年学生对香港政治制度的极大兴趣。[[54]] 何启对英国政治体制以及香港管治架构的阐释,无疑会对孙中山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激发其革新中国旧制的决心。何启“对孙中山在香港的思想形成影响深远”[[55]]。 据何启女婿傅秉常(1896—1965)回忆,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时常谈起受何启教益的种种,自谓其革新思想颇受何启之启发”。“何启著《新政论议》一书,批评清廷者也。总理自谓其学生时代之思想受此书之影响不少。”[[56]]
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之时,可谓满怀救国济民激情,期冀为开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贡献施展才智。此时的他,虽然因为接受基督宗教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而萌生民族主义情绪,因为痛恨清朝政府的愚昧专制统治而点燃革命火种,但更多地表现为一位“改良祖国”的革新者。孙中山以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者形象出现,乃是在其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和平改革梦想破灭之后。此时,距他离开香港已两年之久。
结 语
孙中山在香港求学的9年,乃其早期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其早期思想的核心是救国济民,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具体手段则是“改良”与“革新”。孙中山因仰慕西方现代文明与科学技术而皈依基督教会,因谙熟基督宗教乃西方文明之根而研习西学,因认同西方君主立宪制度而萌生革新中国旧制的思想。此为其早期思想形成之基本理路。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接触西方社会与文化的重要先驱之一。当他对西方的现代化有了一定的认识,再反观中国的苛制虐政,自然会产生民族危机之感和救国济民之情。在香港求学期间,他最先接受的是基督宗教的核心价值。基督宗教信奉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潜移默化地成为他解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及其观念形态的思想基础。对于崇尚现代西方文明与现代化理念的孙中山而言,认同基督宗教的价值观并将之运用于自己的救国济民伟业,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一百多年来,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大多将其定位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然而,“孙中山并非天生的革命者,在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中,曾经受过各种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57]] 在香港求学期间,孙中山自始至终均以救国济民为职志。对其而言,救国济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改良现有政权,另一种是推翻现有政权并重组政府。孙中山的最终理想是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如果不流血即能达此目的,无疑为上上之策。另外,孙中山接受的思想及本人的回应,亦证明其当时的政治取向并非主革命,而只是改革,或曰革新。美国学者史扶邻(Harold Z. Schiffrin)对此的解释是:“作为一名几乎完全西方教育的接受者和现代医学的潜在先驱,孙中山拥有的资历对三合会的吸引力不如对朝廷的进步支持者。他在香港的经历使他意识到这种替代的可能性。这使他对中国的问题有了更广阔的认识,同时也给了他希望:可以献身于改革,而不必成为一个叛乱者。”[[58]] 孙中山从“革新”走向“革命”,事实上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当他竭尽一切和平途径,企图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理想失败之后,才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59]]
孙中山真正公开提出推翻清朝统治、创建共和政府的革命主张并付诸行动,则是发动1895年广州起义的时候。据冯自由言,1895年之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词”。[[60]] “英文革命Revolution一字,旧译为造反。”[[61]] 有学者考证,“孙中山自己对于‘革命’一词的使用,实际上颇为保守。”原因在于,一方面,“在传统语境里,‘革命’与‘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政治文化是连在一起的。无论是造反还是政变,只是推翻旧皇朝的,才能为‘革命’加冕。对于叛乱者而言,自称‘造反’即含有自定的合法性,但未成功之前便称‘革命’,乃不可思议之事。”另一方面,“1895年前后孙中山在香港期间,西方传教士及其对待‘革命’的保守姿态,给孙中山使用‘革命’一词造成重重阻挠。”[[62]] 故此,可以肯定,孙中山香港求学期间所形成的早期思想是以革新为手段、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救国济民思想。
Christianity and the Origin of Sun Yat-sen's Early Thought on Modernization
CHEN Caijun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Sun Yat-sen completed his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years from 1883 to 1892. This period, in which Sun was aged 17 to 26, represented an essential stage for his intellectual accumu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his ideology. Sun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in Hong Kong due to his admiration for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scientific technology. In addition, he devoted himself to studying Western learning during his university years since he knew that Christianity was the roo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Moreover, he developed the idea of reforming the old feudal system in China by identifying himself with the Western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These are the fundamental rationales that shaped Sun’s thoughts. Instead of armed revolution, the core of Sun's early thinking was to save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and bring China onto the road to modernization, with specific methods of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Sun Yat-sen, Christianity, innovation and national salvation, modernization
[[1]] 前人学者对孙中山香港求学时期的研究不乏宏论,如罗香林著《国父之大学时代》(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4年),着重阐述孙中山在西医书院读书时之学习情况及社会活动;黄宇和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 1866—1895》(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中学时代”和“大专时代”两章,详细考证孙中山在香港求学期间的相关史实,厘清他人研究中的某些谬误;莫世祥著《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第一章“君宪革新的滥觞”,指出孙中山在香港求学期间所倡言者尚非“革命”,实为“革新”。然总体而言,罕有学人对中外基督徒于孙中山香港求学期间革新救国思想产生之影响展开深入讨论。
[[2]] 《孙文在大学堂演说》,《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2月21日。另见《在香港大学的演说》(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载林家有编:《孙中山全集续编》第三卷(1921.1—1923.11),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48页;《在香港大学的演说》(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九日),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5页。此演说的日期为1923年2月20日,而《孙中山全集》第七卷根据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2月28日的报道,错误判定为“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九日”。
[[3]] 孙中山:《建国方略》,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9页。
[[4]] 简又文:《国民革命文献丛录》,载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32页。简又文转述关景良回忆。
[[5]] 参见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第47-48页。
[[6]] 陈才俊:《基督宗教与孙中山之“自由、平等、博爱”观》,《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2012年第12期,第112页。
[[7]] 孙中山:《复翟理斯函》,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页。
[[8]] 孙中山:《复翟理斯函》,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页。
[[9]] 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 1866—1895》,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第642页。
[[10]] 香港中央书院1894年更名为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
[[11]] 冯自由:《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历》,载氏著:《革命逸史》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页。
[[12]] 参见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 1866—1895》,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第327、343页。
[[13]] Charles R. Hager, “Dr Sun Yat Sen: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The Missionary Herald, April 1912, p.171. 汉译文见《美国喜嘉理牧师关于孙总理信教之追述》,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页。
[[14]] Charles R. Hager, “Dr Sun Yat Sen: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The Missionary Herald, April 1912, pp.171-172. 汉译文见《美国喜嘉理牧师关于孙总理信教之追述》,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14页。
[[15]] 陆皓东是否领洗加入教会,至今存疑。参见黄宇和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 1866—1895》,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第331—335页。
[[16]] Charles R. Hager, “Dr Sun Yat Sen: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The Missionary Herald, April 1912, p.171. 汉译文见《美国喜嘉理牧师关于孙总理信教之追述》,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页。
[[17]] Charles R. Hager, “Dr Sun Yat Sen: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The Missionary Herald, April 1912, p.171. 汉译文见《美国喜嘉理牧师关于孙总理信教之追述》,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页。
[[18]] 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一九一二年五月七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59页。
[[19]] 孙中山:《复翟理斯函》,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页。
[[20]] 冯自由:《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历》,载氏著《革命逸史》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页。
[[21]] Paul Linebarger, 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25, p.152.
[[22]] 徐弢:《基督教哲学中的灵肉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66、67页。
[[23]] 徐弢:《基督教哲学中的灵肉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68页。
[[24]] 参见陈才俊:《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办及其历史意义》,《高等教育研究》(武汉)2005年第8期,第84-88页。
[[25]] James Cantlie’s speech appeared in China Mail, July 24, 1892. 转引自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第138—139页。
[[26]] 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第135页。
[[27]] 简又文:《国民革命文献丛录》,载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31页。简又文转述关景良回忆。
[[28]] 简又文:《国民革命文献丛录》,载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31页。简又文转述关景良回忆。
[[29]] 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4年,第32页。
[[30]] James Cantlie and C. Sheridan Jones, Sun Yat-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2, pp.202-203.
[[31]] 孙中山:《致郑藻如书》(一八九〇),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
[[32]]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一八九四年六月),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16、17页。
[[33]] 李进轩:《孙中山先生革命与香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第97页。
[[34]] 孙中山:《致郑藻如书》(一八九〇),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页。
[[35]] 孙中山:《农功》(一八九一年前后),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页。
[[36]] 孙日新:《教友少年会纪事》,《中西教会报》(上海)1891年第一卷第5期,第24页。
[[37]] 孙日新:《教友少年会纪事》,《中西教会报》(上海)1891年第一卷第5期,第25页。
[[38]] 孙中山:《复翟理斯函》,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8页。
[[39]][日]宫崎滔天:《孙逸仙传》,《建国月刊》(南京)第五卷第4期(1931年8月),第10页。
[[40]] 《孙文在大学堂演说》,《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2月21日。另见《在香港大学的演说》(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载林家有编:《孙中山全集续编》第三卷(1921.1—1923.11),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48页。
[[41]] 《孙文在大学堂演说》,《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2月21日。另见《在香港大学的演说》(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载林家有编:《孙中山全集续编》第三卷(1921.1—1923.11),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49页。
[[42]] 《孙文在大学堂演说》,《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2月21日。另见《在香港大学的演说》(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载林家有编:《孙中山全集续编》第三卷(1921.1—1923.11),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49页
[[43]] 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一九一二年五月七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59页。
[[44]] 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一九一二年五月七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59页。
[[45]] 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 1866—1895》,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第394页。
[[46]] 《孙文在大学堂演说》,《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2月21日。另见《在香港大学的演说》(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载林家有编:《孙中山全集续编》第三卷(1921.1-1923.11),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49页。
[[47]] 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 1866-1895》,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第379页。
[[48]] 参见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第51页。
[[49]] James Cantlie and C. Sheridan Jones, Sun Yat-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New York: Jarrold & Sons, 1912, p.118.
[[50]]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20.
[[51]] Sinensis, “‘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a Reply to Marquis Tseng,” China Mail, February 16, 1887. 胡礼垣(1847—1916)将此文翻译成中文并阐发己见,定名《曾论书后》,刊载于1887年5月11日的《香港华字日报》。
[[52]] Marquis Tseng, “China, the Sleep and Awakening,’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January 1887; China Mail, February 8,1887.
[[53]] (清)何启、(清)胡礼垣:《新政真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第138-139页;第162页;第165页;第176—177;第179页。
[[54]] G.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A Prpminent Fig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Hong Kong(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6-17.
[[55]]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24.
[[56]] 沈云龙访问、谢文孙纪录:《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10页。
[[57]] 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8页。
[[58]]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24.
[[59]] 参见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 1866-1895》,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第642-643、379页。
[[60]] 冯自由:《革命二字之由来》,载氏著:《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
[[61]] 冯自由:《兴中会组织史》,载氏著:《革命逸史》第四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页。
[[62]]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6、109、112—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