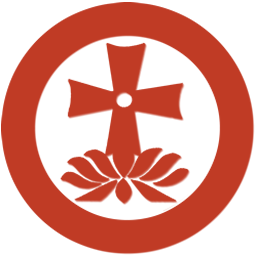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1年第17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138
陈企瑞(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摘要:视觉艺术(visual arts)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的神学阐释及实践中是不可忽略的。在1522年至1545年间,路德针对宗教改革期间的圣像破坏运动,提出了他的神学阐释来表明对视觉艺术的思考和理解;从1519年至1544年,路德参与过的视觉艺术作品直观而具体地反应了路德的视觉艺术理念,从中也可以看到他的态度和立场。本文根据路德对视觉艺术的理论和参与,来分析并解释其历史背景、神学依据并附带一些评论,最后关联路德的视觉艺术与基督教中国化这两个因素,从基督教视觉艺术的题材和形式两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马丁·路德、圣像破坏运动、视觉艺术、基督教中国化
DOI: 10.29635/JRCC.202112_(17).0005
在路德的著作中,视觉艺术(visual arts)似乎不是路德思想的重点,也并非当下研究路德的热门话题。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视觉艺术在路德的神学阐释及实践中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内容,因此,很早以前就有学者涉及到了这个领域。而国内关注这一课题的研究并不多。[[1]] 基于这一现状,笔者尝试挖掘路德的视觉艺术思想及他的参与实践,期待能对当下基督教中国化带来借鉴经验与启发意义。
路德对视觉艺术方面的论述零零星星,碎片化地分布在其讲道词及论道文章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522年,路德从避难所瓦特堡(Wartburg)回到维滕堡(Wittenburg)后公开演说的布道词,以及在1525年,路德立文明确他对圣像或形象的神学理解。另外,从1519年至1544,路德参与过的视觉艺术作品直观而具体地反应了路德的视觉艺术理念,也表明了他对视觉艺术的态度和立场。本文将根据1519年至1545年间路德对视觉艺术的间断性论述和实践参与,进而分析并解释其历史背景、神学依据及一点评析,最后关联路德的视觉艺术观与基督教中国化这两个因素,提出几点思考。
路德与视觉艺术
在路德时期的语境中,视觉艺术指的是教堂内外所有雕刻、铸造、模塑和绘制的各种人物、天使、耶稣和上帝的造型,甚至传道人华丽的礼服和权杖等在内。[[2]] 路德本人并未明确提及“视觉艺术”一词,但他经常使用的圣像(icons),形像(images),雕像等都属于视觉艺术范畴。[[3]]
1525年,路德在讨论圣像的问题前说:“我还未特别对形象一事写过什么,这还是首次。” [[4]] 事实上,路德在1522年大斋节发表的八篇布道词中就有两篇涉及到圣像的问题,他认为圣像是自由的事,而不是必须的事。在第三篇布道词中,路德以《圣经》为例,说明偶像存在的合理性:
摩西岂不是造了一条铜蛇吗(参民21:9)?摩西自己既造了偶像,怎能说他禁止造偶像呢?在我看来,那样的蛇也是一个偶像。我们要怎样回答呢?再者,我们不是读过,在施恩宝座上不是有两只鸟吗(出37:7)?那施恩宝座不就是上帝要受敬拜的地方吗?此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可以造偶像,而且有偶像,但我们不要敬拜它们,若敬拜它们,就要把它们毁坏……保罗在雅典走进庙宇,他没有打坏一个偶像……他宣讲反对他们的偶像,但没有用暴力去推翻一个……。[[5]]
显然,路德对圣像的态度有两方面的,一是废除圣像,因为有人敬拜它们;二是不可废除圣像,因为有《圣经》依据。对于路德来说,尽管《圣经》明言“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但是这个诫命禁止的不是圣像本身,而是人的内心是否将之尊为与上帝同等进而敬拜它们。在第四篇布道词中路德从信仰实际层面进一步谈到:
因为神像都被滥用,所以我愿各处的神像被废除。因为把神像陈列在教堂里的人就自以为服事了上帝,行了善工。这简直就是偶像敬拜……我们必须承认,还有许多人对于神像并无错误观念,所以对他们,神像还是有用的,虽然这样的人为数不多,但是我们对任何有益于任何人的灵修的事不能非难,也不应非难。[[6]]
可以看出,路德辩证地对待神像,他不鼓励设立神像;同时路德又肯定神像具有一定的灵性意义,不应该废除。那么,路德又如何评价破坏圣像的行为呢?
1524年,路德在其 “致施特拉斯堡基督徒的信 -- 反对狂热精神” 一文中,批评了卡尔施塔特(Andreas Bodenstein von Karlstadt, 1486-1541)煽动民众破坏形象的做法。[[7]]而具体从《圣经》依据去论证形象的文章是其1525年发表的 “在形象和圣礼上反对那些天上的先知” 一文。路德在此文中严厉批判目无法纪的圣像破坏者,如卡尔施塔特等人忽略信心的教导,只在乎外在行为。神像是外在的事,而信心才是最重要的,信心也早已胜过了神像带来偶像崇拜的威胁。[[8]] 路德重申要理解旧约里的 “不可雕刻偶像”、 “不可做什么形象”、“不可跪拜那些像” 的真实意义,必须联系上下文,这些禁令都是针对上文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20:3)而言的:
因为“你不可有别的神”的话,乃是中心思想,是标准和主旨,其后所有的字句,都必须按照这些话来解释,联结和判断。因为这经句是将这条诫命的意义,指出并表达了出来,就是不可再有别的神。故此,不管其后跟着的是“做”、 “形象”或“事奉”等等字句,都不可理解为别的意思,而只含有不可从中发展出来假神崇拜和偶像崇拜的意思。甚至“我是你的上帝”的话(出20:2),也是一切论及崇拜和事奉上帝的话之标准和主旨。[[9]]
所以,“做的形象” 如果不是用来崇拜的,就不应被禁止,“那些毁坏形象的人也应当包容我保存、佩带、观赏十字架,或圣母像,甚至偶像的形象,这完全符合最严厉的摩西律法,只要我不是崇拜它们,仅用作纪念的话。” [[10]]人们只要靠着上帝的道,仰赖基督,在这之外,都是可被容许的,“为纪念和见证作用的形象,如十字架、圣徒的像之类的,是当容忍的……甚至摩西律法也是容许的,它们也有存在的价值,值得尊重……” [[11]] “我希望准许我们将这些书上的图画在墙上,作为纪念和更易了解。” [[12]] 这里路德具体指出形象的类型,肯定其作为 “纪念” 和使人 “更易了解” 即教导的功能。在1529年的“圣徒受难记”一文中,路德补充道:“对于小孩和单纯的人,教导他们上帝之事借助于形象或样式要比仅仅通过使用话语和教导更有效。” [[13]] 当时有人担心神像有可能引起偶像崇拜,路德回应,上帝之道的权柄早已胜过神像的影响力。[[14]] 如同上文提到的,信心胜过神像,在路德看来,上帝之道、信心应该是神像的规范和前提,可确保信徒不陷入偶像崇拜。
然而,有些形象确实被用来当作偶像崇拜,这又该如何解决呢?路德同意废除这些形象,但是废除过程必须有秩序,配合掌权者执行:“为此,我们常常在旧约中得到,每当除去形象或偶像的时候,并不是由民众,而是由掌权这去做的,正如雅各埋他家的偶像(创35:2-4)、基甸受上帝的呼召作首领之后拆毁巴力的坛(士6:25)、西希家王也是如此打碎铜蛇的(王下18:4)……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每当上帝吩咐某一团契和人民去作什么,他不是要民众撇开掌权者,乃是藉着掌权者和他的民众一起完成。”。[[15]]
除了文字的论述,路德也亲自参与或实践在视觉艺术作品中。1522年之前,路德虽未正式论及视觉艺术,一幅路德的肖像画却表明了他的态度。1519年,路德的好友兼维滕堡的宫廷画家、德国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后担任维滕堡市长的老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1472-1553)为路德画像(图1),画中的路德像是受圣灵感动,正在宣讲真理福音的年轻人模样。[[16]] 此后,老克拉纳赫陆续为路德及其家人作画多幅,包括目前使用频率较高的路德肖像画(见图2、3,分别为1528年、1529年所画)。[[17]] 可以说,没有老克拉纳赫的肖像画,就无人知晓路德的真面目。[[18]] 1530年,在萨克森选候约翰·腓德烈(John Frederick the Magnanimous,1503- 1554)的授意之下,纽伦堡(Nuremberg)的改教家史彭格勒(Lazarus Spengler, 1479-1534,路德的忠实支持者)为路德设计一枚印章,后被称为 “路德印章(Luther Seal)” 或 “路德玫瑰(Luther Rose)”(见图4),[[19]] 当路德收到设计图后非常满意,认为此图恰好表达了他的神学理念。1530年7月8日路德写信给史彭格勒,阐释了此图的神学意义。[[20]] 1544年10月5日落成的德国第一座新教教堂,也是路德平生唯一一次祝圣的教堂:托尔高城堡教堂(the Electoral Schlosskapelle of Hartenfels, Torgau)。(见图5)托尔高教堂具有德国萨克森高地独特的本地建筑风格,[[21]]内部的雕刻艺术体现了路德的神学中心。最为典型的就是正对教堂大门北墙上的讲坛(pulpit,见图5右侧墙),鼓形表面有三幅彩色浮雕,分别取材于《圣经》中耶稣的故事(见图6、7、8),从左向右依次为耶稣赦免行淫妇女 -- 体现 “唯独恩典”(sola gratia)、孩童耶稣在圣殿里 -- “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耶稣洁净圣殿 -- “唯独信心”(sola fide)。这三幅雕塑恰恰是路德改教的三大原则。[[22]]
1 2 3 4 5 6
7 8
这些作品形象具体地展现了路德的视觉艺术理念,路德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及实践视觉艺术与他对视觉艺术的文字论述是相一致的。当代研究学者斯克里布纳(R. W. Scribner)对路德的视觉艺术总结道:“视觉艺术可以用来教导;也可以作为信仰的示范,及路德教义的见证;严守以 ‘上帝之道’ 为标准和规范的基础上,视觉艺术具有指导的意义和价值。”[[23]] 因此,路德对视觉艺术观点可以归纳为:1. 神像是可以容忍的,只要不用来与上帝同等崇拜;2. 神像具有纪念、灵修、见证、教导的功能;3. 与信心、恩典、《圣经》、基督、上帝之道相关的神学主题是视觉艺术的前提和规范。
路德的视觉艺术之评析
路德讨论视觉艺术有其历史背景和神学根据。他的初衷在于平息圣像破坏运动引起的骚乱,而他在论述过程中,始终以他的改教原则为基础,围绕他的神学中心展开的。
1、历史背景
16世纪新教的圣像破坏运动(Iconoclasm)的范围是史无前例的。最早记载宗教改革时期的圣像破坏事件发生在1521与1522年间的维滕堡。1521年4月-1522年2月,路德离开维滕堡之际,当地的宗教改革由维滕堡城堡教堂会吏长的卡尔施塔特、维滕堡大学的希腊文教授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以及路德所属的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慈威凌(Gabriel Zwilling, 1487-1558)负责。在卡尔施塔特的倡导下,维滕堡市议会命令挪去教堂里的圣像,并将风琴、喇叭、笛子等乐器也移除出去,他认为,《圣经》明言“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因为上帝是个灵”;慈威凌也受鼓动,领导民众推翻祭坛,捣碎圣徒肖像和图像,移除风琴、喇叭、笛子等乐器。[[24]] 于是,整个维滕堡小城失去控制,处于骚乱局面,年轻的梅兰希顿将此形势告知路德,路德心急如焚,匆匆赶回城。路德回来之后,针对旧约十诫的禁令来解释偶像崇拜与神像设立是非对等关系,渐渐平息了维滕堡的圣像破坏运动。然而,卡尔施塔特离开维滕堡之后,在施特拉斯堡(Strassburg)宣传他对神像和圣礼的观点,引起当地教会动乱。因此,布塞尔(Martin Bucer,1491-1551)等当地传道人致信给路德,期待获得支持。1524年,路德写信给施特拉斯堡的信徒未有详尽的驳斥,而1525年的 “在形象和圣礼上反对那些天上的先知”便是对前面信件的详细回应,“天上的先知” 具有讽刺意味,指卡尔施塔特和他的跟随者。圣像破坏还导致以艺术为生的画匠、手工艺者失去经济来源,同时也招致人文主义者(humanists)对新教徒的批评,他们上诉政府,要求采取措施加以制止。[[25]] 但是市议会也束手无策,因此他们不得不邀请路德回到维滕堡,主持大局。从这一史实来看,路德在视觉艺术问题的处理上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文化层面乃至社会稳定,而不仅仅简单的宗教意义。
除了卡尔施塔特等人反对神像,瑞士改教家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 1484-1531)也对此深恶痛绝。1524年苏黎世议会下令废除所有圣像,全城教堂一律禁止设立神像。[[26]] 这次圣像破坏运动分为两波,第一波发生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的德国和瑞士;第二波发生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苏格兰、法国的部分地区与荷兰地区,这些地区的圣像破坏运动与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传播和政治宗教叛乱并行。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本人也反对神像。而相较于茨温利与加尔文及其影响的教会,路德与其跟随者对视觉艺术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教堂内外的历史文物。时至今日,部分保存下来的作品反映了16世纪的德国社会状况,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源和珍贵的艺术瑰宝。
2、神学依据
路德的视觉艺术理念背后充斥着五个神学关键词:《圣经》、信心、恩典、基督、上帝之道,其中《圣经》是最为根本的。正如阿尔托依兹(Paul Althaus)所分析的:“路德所有的神学思想都以《圣经》为先决条件。” [[27]] 圣像破坏者的主要依据来自《圣经》中“十诫”对雕刻偶像的禁令。路德也以此处经文着手,解释偶像存在的合理性。“不可有别的神”是路德对禁令的理解,这透露出对独一上帝的信心,这个信心早已胜过神像带来的影响。如果说路德的肖像画表明路德对视觉艺术的态度的话,那么 “路德玫瑰” 与托尔高教堂的浮雕则集中了路德的神学思想。前者折射出路德的信仰、十架的救赎恩典;后者围绕 “唯独恩典” 、 “唯独《圣经》” 、 “唯独信心” 主题的叙事图像更是反映了以基督为中心的,以上帝之道为准则的改教原则。托尔高教堂讲坛上的神学旨趣也反复出现在老克拉纳赫视觉艺术作品中。伊萨阿兹(Vera Isaiasz)指出,关于律法与福音,基督赦免行淫妇女的主题作品经常被使用且重复出现在视觉艺术创作中。[[28]] 这说明路德的视觉艺术神学依据与当时德国宗教艺术作品已经产生发酵性和互动性的反应。而这个神学依据按照拜尔(Oswald Bayer)的理解,可以用一句话表达:“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加5:13)” 。[[29]] 这样的神学表达离不开《圣经》、信心、恩典、基督、上帝之道这几个因素。《圣经》启示,透过信心的渠道,确认得到救赎的恩典 (或也可理解为 “因信称义” ) ,上帝之道便是《圣经》的话语和基督自己。而救赎的实现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加5:1)。上文已经提及路德指出神像是自由的事,而非必须的事。被蒙召和救赎的基督徒已经获得自由,不必在个人可自由取舍的事上产生矛盾和冲突。魏玛(Christoph Weimer)就有类似评论:“路德认为神像的存在,是可行可不行之事(adiaphora)。” [[30]] “所谓可行可不行之事” 指的是一些教理与道德伦理的实践在《圣经》中没有明确禁止或必须遵行的。这样的事是基督徒可以自由取舍的。
表面上,路德与卡尔施塔特等人的矛盾源于对视觉艺术的不同看法,但其实质矛盾在于二者对《圣经》的不同解释及神学落脚点各异。前者主张多重释经方法,从字面文本到《圣经》历史再到经文意义,路德的释经更强调在基督里的信心;后者拘泥于个别文字本身的意思,割裂《圣经》文本的整体意义,把灵性和物质相对立,卡尔施塔特注重“上帝是个灵”的灵性主义(spiritualism),拒绝可见的神像。进一步而言,二者的神学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见解。狄林贝格(John Dillenberger)认为路德对视觉艺术的理解十分宽泛,他对《圣经》和对视觉艺术的解释都是借着信心的想象来表达的,而这种表达可能还超乎于现实意义。[[31]] 换句话说,路德对视觉艺术的解释融合《圣经》和信心,具有更多的神学想象,而这种想象是具有纪念、灵修、见证、教导等方面超现实的灵性意义的,目的旨在引导信徒更好地坚固信心,深切体会基督的救赎恩典,在上帝之道的真理中越发进深而得造就。所以,路德的视觉艺术理念始终围绕《圣经》及其紧密关联的神学关键词而进行论述和实践的。
3、评论
对于圣像破坏运动,路德是极其苦恼伤神的。培登(Roland Bainton)就这一事件评论道:“这些破坏神像的暴行,在路德看来比教皇曾加于他的都大。他开始体会到他与罗马也许比与他自己那些分离分子毕竟更加接近。” [[32]] 这说明,圣像破坏运动并非路德改教的边缘事件,而是影响改教同盟阵营分裂的重大问题。路德在其神学框架内阐释视觉艺术的合理性存在,为基督徒找到了信仰依据;同时,路德也把视觉艺术的神学理论局限在“路德式的”神学领域里,而这也导致他与“非路德式的”阵营越走越远。与“卡尔施塔特式的”灵性主义者的分离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基督教历史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圣像破坏运动,前两次分别为八、九世纪拜占庭发起的圣像破坏运动。第三次就发生在路德时期。路德偶有提及东方发生过的圣像破坏运动,[[33]] 但并未吸收东方的圣像神学理论,而是沿袭了西方教会大格列高利(St. Gregory, the Great, 约540-604年)关于圣像具有的教导等意义的传统。[[34]] 东方教会于787年召开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会上确立圣像崇拜的规定,这个决议精神源自于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 675-749)等人的神学主张。约翰的圣像神学根基在于道成肉身的见证:“现在他已经藉着肉身有形有体地显现,与人同住,因此我可以用我所看到的,来为神制成肖像,对着已经被揭开神秘面纱的主,默想他的容美。” [[35]] 道成肉身使不可见的上帝成为可见的样式,无限的超越者成为有限的物质形体。基督道成肉身便是圣像崇拜的神学基础。人们通过物质图像想起物质的创造者,道成肉身便是对神像的肯定。路德的视觉艺术虽然以基督为中心,却只是继承西方教会的圣像传统理念,未能吸取东方教会道成肉身的神像神学诠释。从这一角度来说,路德对视觉艺术的神学理解缺乏大公性。
在路德的诠释下,德国路德宗教会的视觉艺术围绕着路德神学进行创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克拉纳赫父子。但是,偏向于某一方面就有可能顾此失彼。德国艺术领军人物蒂西欧(Georg Dehio)评论道:“从历史的、客观的角度来说,(德国宗教改革的艺术)事实上导致了德国艺术走向衰退”; 席勒格(August Wilhelm Schlegel)批评路德影响下的视觉艺术“扼杀”了画家的手工艺;科尔讷(Joseph Koerner)也认为用于宣传路德神学的“缺乏美学价值,没有视觉魅力,缺少情感流露。” [[36]] 一方面,对于路德宗艺术家而言,他们并非缺乏专业艺术美学知识(如如老克拉纳赫曾在维也纳多瑙河学校专攻风景画技艺),但视觉艺术本身价值不是他们创作的旨趣。另一方面,受路德神学影响的视觉艺术的主要目的在于宣传路德的教义和改教的精神,美学和艺术价值必须从属于神学表达,两者融合过程中,他们可能不得不牺牲艺术中来自经验直觉的视觉吸引力和情感散发力。另外,路德的宗教改革将德国基督徒从教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信仰成为个体性的宗教事务,不再受教廷束缚,这一举措觉醒了德意志的民族自尊和独立意识。但在视觉艺术理念上,路德并未融入这一点。若能在《圣经》的基础上把圣像作为德意志民族性的文化遗产,结合民族意识来说服他人,民众是不是不至于那么容易被煽动而大规模破坏圣像呢?
路德对视觉艺术讨论出于形势的需要,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层面,限于篇幅,本文不便展开论述。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圣像破坏者并不反对所有的视觉艺术,而是拒绝在教堂和信仰生活中运用艺术作品。因此,圣像反对者仅仅是从宗教层面考虑,而路德却不得不从全局来考虑,尽管有其神学或艺术视野的局限性,但从当时的局势来看,路德对视觉艺术的处理或许已是所有可能中最切实的阐释。
路德的视觉艺术与基督教中国化
将路德的视觉艺术与基督教中国化两者结合起来探讨,首先需要寻找二者的关联性和契合点,也就是探讨的可能性,有了这个前提,才能寻找其中有否可借鉴的、适切的实践意义。因此,下文就两者之间的关联和实践两部分进行论述。
1、路德的视觉艺术与基督教中国化的关联
首先,路德的神学与中国基督教(新教)信仰的契合度。上文已有总结,路德的神学中心可表达为:以《圣经》为先决条件的信心、恩典、基督、上帝之道这几个关键词。而这也正是中国教会信仰的表达中心,两者有着不言而喻的亲和力。中国教会绝大数人都会接受路德提倡的 “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 思想,信徒高举基督的权威,以上帝之道为中心。教会也经常把上帝之道理解为《圣经》,因《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提后3:16)《圣经》里有永生之道,(约6:68,14:6)因此中国基督徒 “爱《圣经》,也研究《圣经》” [[37]] 同时,一些基督徒也习惯性地因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出20:4)的诫命或相关经文而拒绝在教堂里或家里摆设绘画图像等视觉艺术作品,甚至毁坏家中一些珍贵的艺术作品。而路德从《圣经》出发的神学解释,为视觉艺术找到了合乎信仰的理由。只要不将视觉艺术作品视为与上帝同等去跪拜的,就不违背信仰,不能称之为偶像崇拜。因此,路德对视觉艺术的神学阐释是适合中国教会的信仰表达的,而基督教中国化恰恰也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即以《圣经》为依据的。[[38]] 这就更强化了讨论路德的视觉艺术与基督教中国化两者的契合度。
其次,基督教中国化的大众性。基督教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基督徒,实践的主体也应该是教会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39]] 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理念最后必然落实在实践中,而实践的过程需要大众的参与。路德提出视觉艺术的功能,所指的对象便是普通基督徒大众。他们有些不认识字,但可以通过图像理解信仰。对于当时的路德来说,视觉艺术中可以使信徒得到灵性的操练、受到信仰见证的鼓舞、引导信徒正确地认识真理等等。而视觉艺术的这些功能,在中国教会中也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在关于上帝形象的视觉艺术作品中加入中国元素,可以表达上帝不仅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也是中国人的上帝,这样,在可视的中国元素的作品中,基督徒的中国身份意识可以自然而然地得以提高。如果路德时期的视觉艺术作品指向大众化的雕刻、铸造、模塑的话,那么今天中国教会的视觉艺术可以更加多元化和现代化,比如动态的影视视觉艺术,借助网络大众媒体传播工具,有效地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因此,从基督教中国化的大众性来说,视觉艺术可以并且也应该成为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途径。
最后,基督教需要中国化的文化表达。基督教中国化有其文化要素,也就是文化方面的基督教中国化。[[40]] 而视觉艺术则在文化领域里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路德时代,以老克拉纳赫为代表的德国文艺复兴艺术家并未完全承袭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创作特征,而是根据本土文化设计视觉艺术作品,如托尔高教堂就凸显出萨克森高地 “学院派” 的艺术风格,利用当地文化表达基督教的信仰精髓。在这点上,中国基督教也可以本土化来体现身为中国宗教的独特之处。这里的本土化除了汉族,也包括各个少数民族的本土文化;同时不可忽略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佛道教和各种民间宗教的信仰表达。
2、具体实践
视觉艺术是基督教展现自我有效的手段和方式,在基督教中国化的命题下,基督教的视觉艺术担负着信仰教导和信仰的中国化表达之双重使命,具体的实践可从视觉艺术的题材与形式两方面入手。
题材:无论哪一类基督教视觉艺术首先应具有本宗教信仰的特点,体现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传统教义及相关主题。路德的视觉艺术以《圣经》为先决条件,那么,在以《圣经》为前提和基础的基督教中国化视野下,《圣经》内容显然为十分恰当的题材。取材于《圣经》的视觉艺术更能够为教会大众所理解和接受。比如围绕耶稣生平与救赎的内容,又比如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叙事情景,《圣经》里各种人物及其见证等等;除《圣经》题材之外,教会历史,比如各地教堂有其各自的发展历史,创作与该教堂历史发展相关的题材能为本堂信徒找到身份归属感,同时令他们真实地体会到基督的身体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形有体地建立起来的见证,教会的建立是有历史传承的,这一点能够消除一些信徒的历史虚无主义。
形式:视觉艺术的形式不胜枚举,这里仅列举若干例子:
建筑: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基督教一直在兴建教堂,教会不遗余力地探索能够体现中国基督教自我身份的教堂建筑。教堂建筑需要融入中国建筑艺术的特点。富有艺术感的中国建筑可以归纳为五个基本特色:“屋顶、斗拱、台基、色彩和均称的平面布置。” [[41]] 屋顶通常为曲面,屋檐四角翘起,即“飞檐”,起到透光和往外泄雨的功能。斗拱起到支撑屋顶和屋外立柱间的托起功能;台基相当于建筑的基座。梁思成解释说,一个台基、一个外檐伸出的坡形屋顶的建筑,适合于任何华夏文明所及之处。[[42]] 而色彩上以彩绘为主要形式,一般彩绘用于檐下结构部分,在阴影掩映之中。主要彩色以 “冷色” 如青蓝碧绿,有时略加金点。其它檐以下的大部分颜色则纯为赤红,与檐下彩绘正成反照。平面布置是本着均衡相称的原则,左右均分的对峙。[[43]] 若要体现教堂建筑视觉艺术的中国特征,或许上述五个特色可以带来启发。
书画:书法与绘画集中体现出中华民族高超的艺术造诣。中国书法可以说是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教会已有不少基督徒书法家致力于书法创作,这对弘扬中国民族文化,实现基督教中国化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国绘画中山水画尤其能表达了中国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这也是中华民族艺术精神的体现。运用山水画描绘上帝创造自然的情景或作为各种叙事背景,均能给人留下中国化视觉的印象。另外,体现中国文化传统特征的佛教绘画不可忽视,尤其是其表现生活中的欢乐与苦难、情感与希望,表现人们坚强、镇定、忍耐、牺牲的宝贵品格的作品,[[44]] 值得基督教借鉴和参照。
雕塑:雕塑既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标志和象征,也在诉说民族发展的历史和演变,中国雕塑自古就有纪念性的、宗教性的和民间风俗的特点,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雕塑,三重特点都能够用于基督教领域内,可分别发挥纪念见证、信仰教导、融入大众的功能。
其它:根据马特兰(Thomas R. Martland)对艺术的介绍,除了建筑、绘画、雕塑、等形式,舞蹈、戏剧和歌剧都应该属于艺术范畴。[[45]] 显然,舞蹈、戏剧、歌剧同时具备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的特征。其中,戏剧中的戏曲是中华民族的国粹,为中国人喜闻乐见,具有大众性和民间性,如京剧、越剧、黄梅戏、昆曲等等各样形式的戏曲剧种带着浓厚的故乡情,极其容易唤起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基督教的舞台艺术十分丰富,借着中国戏曲的形式表达对信仰的理解,观者对基督教的亲切感必定油然而生。舞台戏曲属于动态的视觉艺术,类似的还有影视动画作品很值得基督教研究和运用。此外,民间的手工艺品,如剪纸、刺绣、织锦也都可以被用来传达基督教的思想。
上文已经提及,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主体是教会群体,教会在视觉艺术的各个领域里人才济济,视觉艺术的创作者不一定是高学历受过专业理论训练的人,他们可以是具有家族相传或师承下来的某一特殊手艺,也可以是有一定水准的、有业余爱好的个人。教会可以充分调动这些创作人的积极性,鼓励他们能够创作出反映中国传统文化或当地民间习俗的作品。
总结
路德对视觉艺术辩证性的论述为基督教的视觉艺术提供了圣经基础和神学依据。今天,中国基督教可以根据路德的视觉艺术思想发掘出既能传达基督教信仰,又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视觉艺术作品,这样,带有中国艺术特色的建筑、雕塑、书画、戏曲等基督教视觉艺术作品能够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发展的务实性和普及化,这不仅丰富了中国基督教的神学表达方式;也有助于教会讲好中国基督教自己的故事,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全球化不断加速的进程中,在中国不断走向世界的时代契机中,中国基督教在视觉艺术的创作上可以充分发挥中华大地多民族、多元化、多样性、包容性的海纳百川之中国气度,体现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展现中国基督教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独特风采。
参考书目
《马丁·路德文选》,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小组 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路德文集》(卷二),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 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阿尔托依兹,保罗(Paul Althaus):《马丁·路德神学》,段琦、孙善玲 合译,新竹:信善神学院,1999年。
丁光训:《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
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林徽因:《林徽因谈建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
马特兰(Thomas R. Martland):《宗教艺术论》,李军、张总 译,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
迈尔斯·玛格丽特(Margret R. Miles):《道成肉身:基督教思想史》,杨华明、李林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麦葛福(Alister E. McGrath)编:《基督教原典菁华》,杨长慧 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
罗伦·培登(Roland Bainton):《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陆中石, 古乐人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年。
周施廷: “克拉纳赫与马丁·路德肖像画”,《美术学研究》,2015第4辑。
卓新平:“基督教‘中国化’的再思考’”,引自《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二辑),张志刚、唐晓峰 主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
Martin Luther, “Passional” in Luther’s Works: Volume 43, ed. by Helmut T. Lehmann, tran. by Jaroslav Pelika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68.
Martin Luther, “Letters” in Luther’s Works: Volume 49, ed. by Helmut T. Lehmann, tran. by Gerhard A. Krodel,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72.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Volume 32 (German Edition) , Charleston: Nabu Press, 2012.
Bayer, Oswald, Martin Luther’s Theology: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trans. by Thomas H. Trapp,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8.
Dillenberger, John, Image and Relics: Theological Perceptions and Visual Images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 Oxford: Oxford Unviersity Press, 1999.
Isaiasz, Vera, “Early Modern Lutheran Churches: Re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Holy and the Profane”, in Lutheran Church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 by Andrew Spicer, Farnham: ASHGATE, 2012.
Koerner, Joseph, The Reformation of the Image, London: Reaktion, 2004.
Heal, Andrew Bridget,“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s, ed. by Ulinka Rublac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5.
Scribner, R. W., “German Renaissance Architecture by Henry-Russel Hitchcock”, in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56, No. 1, 1984.
Scribner, R. W., Popular Culture and Popular Movements in Reformation Germany, London: The Hambledon Press, 1987.
Weimer, Christoph, “Luther and Cranach on Justification in Word and Image”, in the Pastoral Luther: Essays on Martin Luther’s Practical Theology, ed. by Timothy J. Wengert et al.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7.
傅先伟:“纪念丁光训主教诞辰10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登陆于2017年10月6日,http://www.ccctspm.org/news/ccctspm/2015/925/15925928.html.
克拉纳赫作品数据库,登陆于2017年10月4日,www.lucascranach.org.
Matin Luther’s view on Visual Arts and Sinicization
CHEN Qirui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
Abstract: Martin Luther (1483-1546) never uses the term “visual arts”, which, remains indispensable for his theological articulation and practice. Since 1522, the Iconoclsam under the Spiritualists had caused social turbulence in Wittenberg and the other places in Europe. Luther set forth his view on visual arts defending against that radical deed. Through the Biblical interpretations and theological treatises, Luther had made the social situation stable successfully. In Luther’s discussion from 1522 to 1545, we find his dialectical,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attitude and position on visual arts. For Luther, visual arts could be used in church life as far as they were regarded as a way of understanding belief, rather than al. According to Luther’s view on visual arts, this paper displays the analysis of his historical backdrop, theological foundation and some assessment, as well as applies Luther’s on visual arts into the modern context in China. In doing so, it demonstrates that Martin Luther’s idea of visual arts can be utilized for the exploration of Christian Sinicization today.
Key words: Martin Luther, Iconoclasm, visual arts, Chinese Christianity
[[1]] 英语世界有学者发表相关著作或论文,比如,Christensen, Carl: Art and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1979); Scribner, R. W.: For the Sake of Simple Folk: Popular Proganda for the German Reformation (1981) & Popular Culture and Popular Movement in Reformation Germany (1987); Koerner, Joseph Leo.: The Reformation of the Image (2004); Smith, Jeffrey Chips: German Sculpture of the Later Renaissance, c. 1520-1580: Art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1994); Dillenberger, John: Image and Relics:Theological Perceptions and Visual Images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 (1999); Pettegree, Andrew: “Art” (2000); Heal, Andrew Bridget: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 (2017),等等。国内学界有少数学者涉及到路德与视觉艺术的关系。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周施廷教授在2015年发表的 “克拉纳赫与马丁·路德肖像画”、2008年“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木刻画宣传版画中所反应的路德形象”;北京服装学院党楚欣在其硕士论文中(2018年)论述老克拉纳赫与宗教改革的图像宣传,其中有涉及部分路德的视觉艺术理念。
[[2]]《路德文集》(卷二),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28页。
[[3]] 中文翻译中也使用“偶像”、“神像”、“肖像”、“图像”,下文这些词都指向视觉艺术。
[[4]]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在形象和圣礼上反对那些天上的先知”,引自《路德文集》(卷二),第136页。
[[5]]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论自由 -- 婚姻与神像”,引自《马丁·路德文选》,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小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
[[6]] 马丁·路德: “论自由 -- 拜神像与吃祭牲”,,第109页。
[[7]] 马丁·路德: “致施特拉斯堡基督徒的信 -- 反对狂热精神” ,第121-127页。
[[[8]]] 马丁·路德: “在形象和圣礼上反对那些天上的先知”,第132-134页。
[[9]] 路德使用大量经文作为论据说明崇拜与事奉上帝的话这一宗旨。如“关于这一点,我有一节极有力的经文记在《利未记》二十六章1节:‘你们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錾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同样《申命记》四章15节等所谈到的禁止制造形象,也清楚地说明与崇拜相关。”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在形象和圣礼上反对那些天上的先知”,引自《路德文集》(卷二),第138-139页。同参1529年路德所写《大教理问答》上对第一诫命的解释。
[[10]] 马丁·路德: “在形象和圣礼上反对那些天上的先知”,第140页。
[[11]] 马丁·路德: “在形象和圣礼上反对那些天上的先知”,第144页。
[[12]] 马丁·路德: “在形象和圣礼上反对那些天上的先知”,第149-150页。
[[13]] Martin Luther, “Passional” in Luther’s Works: Volume 43, ed. by Helmut T. Lehmann, tran. by Jaroslav Pelika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68), 11-45. 在1533年,1537年,1538年,及1545年,路德都有类似的论述,肯定神像的教导意义。可参:魏玛版《路德文集》,37、46、47卷。
[[14]] Andrew Bridget Heal,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s, ed. by Ulinka Rublac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5), 606.
[[15]]马丁·路德: “在形象和圣礼上反对那些天上的先知” ,第142页。
[[16]] 画中四周环形内的文字从右往左分别为:马丁·路德博士、奥古斯丁会修士、维滕堡,这幅最早的路德肖像画见于同年出版的《在莱布斯克的布道》(Ein Sermon geprediget zu Leypassgk)一书的封面。参:周施廷: “克拉纳赫与马丁·路德肖像画”,《美术学研究》,2015年第4辑,第336页。路德肖像亦来自此文。
[[17]] 老克拉纳赫在改教运动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他支持路德出版德文《圣经》,发行改教宣传刊物,他的很多绘画雕刻作品都体现了路德改教的中心思想,也反应了16世纪德国的社会变迁。在维滕堡市政厅广场南侧的 “克拉纳赫之屋” 陈列许多艺术作品(有些为复制品),广场东侧的圣玛丽教堂祭坛上陈列他的绘画,教堂右侧的画廊作品也很值得研究。他的儿子小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Younger, 1515-1586)的艺术作品也体现了路德的神学思想,如陈列在维滕堡路德故居中的绘画:“耶稣受难像”(Crucifix, 作于1571年)。两幅肖像画来自克拉纳赫的作品数据库:www.lucascranach.org。
[[18]] Christoph Weimer, “Luther and Cranach on Justification in Word and Image”, in the Pastoral Luther: Essays on Martin Luther’s Practical Theology, eds. by Timothy J. Wengert et al.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7), p.292.
[[20]] 路德在信中写道:“心形里自然色的黑十字架,提醒我在被钉十字架基督里的信心拯救了我……这的确是黑色的十字架,使人感到羞辱、带来痛楚的十字架,但它依然以本色留在心里。它不会扼杀生命,相反地,它使人得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矗立在白色的玫瑰中,显出信心带来喜乐、安慰与平安。白色也代表灵魂和天使的颜色,象征着灵魂与信心里的喜乐是将来属天喜乐的开端,这份喜乐已经开始,在盼望中已经被抓住,只是还没启示出来。外部的金色圆环象征天上的祝福源源不断、永无止尽。这个福分如此美妙,超越一切喜乐与美善,如同金子是最贵重和最珍贵的金属一样。这也是对我神学的总结。Martin Luther, “Letters” in Luther’s Works: Volume 49, eds. by Helmut T. Lehmann, tran. by Gerhard A. Krodel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72), p.356-359. 玫瑰背景的蓝色象征天上。图案中的玫瑰雏形可能来自1519年,路德发表的一篇讲章册子封面,作品带有木刻玫瑰的图样(见文中图1)。在艾斯勒本(Eisleben)的路德故居通往附近教堂的青石路上、石阶上都刻有路德玫瑰的图案,现今,路德玫瑰已经成为路德宗的标记。
[[21]] 受德国文艺复兴影响,托尔高教堂属于萨克森高地晚期哥特式传统,这种传统风格以冷色调为主,显示出庄严肃穆的“学院派”特征。参:R. W. Scribner, “German Renaissance Architecture by Henry-Russel Hitchcock”, in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56, No. 1(1984): p.175.
[[22]] 托尔高的城堡教堂长宽高分别为23*11*14(米),内部小巧朴素,为了与天主教恢弘气势、色彩华丽的风格区分开来,祭台显示少有的简洁,管风琴也是到了1944年才配备的。教堂落成当天,路德上下午讲了两场道,上午的讲道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路德提出了对教堂崇拜的定义,这成为日后基督教对崇拜理解的典范。讲章可参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Volume 32 (German Edition) ( Charleston: Nabu Press, 2012), pp. 588-615. 图5见http://www.sachsen-tourismus.de/en/. 图6-8由友人在托尔教堂内拍摄发至笔者。
[[23]] R. W. Scribner, Popular Culture and Popular Movements in Reformation Germany, (London: The Hambledon Press, 1987), p. 338.
[[24]] 罗伦·培登(Roland Bainton):《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年,第185-186页。
[[25]] Andrew Bridget Heal, 602-603.
[[26]] Andrew Bridget Heal, 602.
[[27]] 保罗·阿尔托依兹(Paul Althaus):《马丁·路德神学》,段琦、孙善玲 合译,新竹:信善神学院,1999年,第19页。
[[28]] Vera Isaiasz, “Early Modern Lutheran Churches: Re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Holy and the Profane”, in Lutheran Church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 by Andrew Spicer (Farnham: Ashgate, 2012), 22.
[[29]] Oswald Bayer, Martin Luther’ Theology: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trans. by Thomas H. Trapp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 2008), xvi.
[[30]] Christoph Weimer, “Luther and Cranach on Justification in Word and Image”, in the Pastoral Luther: Essays on Martin Luther’s Practical Theology, eds. by Timothy J. Wengert et al.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7), 296. 这一词出自于以梅兰希顿为代表的路德宗教会试图与天主教和解而提出的一些礼仪教理等方面的事相关。可参考《奥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
[[31]] John Dillenberger, Image and Relics: Theological Perceptions and Visual Images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 (Oxford: Oxford Unviersity Press, 1999), 190.
[[32]] 罗伦·培登(Roland Bainton):《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年,第192页。
[[33]] 路德提到东方教会的圣像争论者把自由的事当作必须的事。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论自由 -- 婚姻与神像”,第107页。
[[34]] 参玛格丽特·迈尔斯(Margret R. Miles):《道成肉身:基督教思想史》,杨华明、李林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56页。
[[35]] John of Damascus, “contra imaginum calumniators”, I, 16, 转引自《基督教原典菁华》,麦葛福(Alister E. McGrath)编,杨长慧 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第194页。
[[36]] 三种批评观点都引自Joseph Koerner, The Reformation of the Image (London: Reaktion, 2004), 28-29.
[[37]] 丁光训:《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38]] 傅先伟:“纪念丁光训主教诞辰10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http://www.ccctspm.org/news/ccctspm/2015/925/15925928.html。
[[39]] 这并不具有排他性,不是否认教外对基督教中国化的参与和研究,相反地,正是因为当下教外人士对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和关注,促使中国基督教进一步思考,如何立足自身信仰,从基督教作为中国宗教的本位出发,与学界、与社会进行对话和交流,以获得更多人的理解。
[[40]] 卓新平:“基督教‘中国化’的再思考’”,引自《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二辑),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8页。
[[41]] 林徽因:《林徽因谈建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8页。
[[42]] 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4页。
[[44]] 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1页。
[[45]] 参马特兰(Thomas R. Martland):《宗教艺术论》,李军、张总 译,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