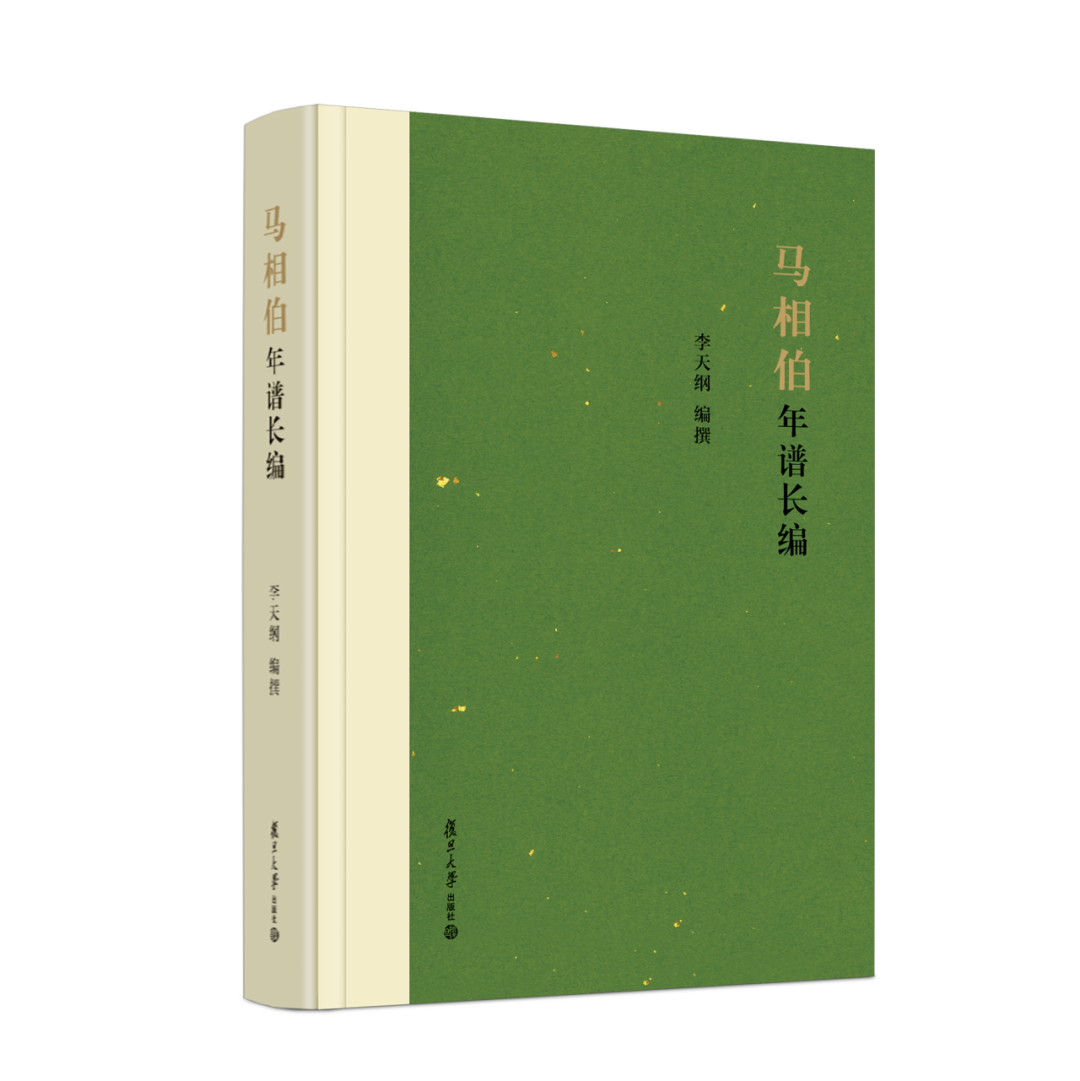
李天纲 编撰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5年8月
| 本书简介 |
本书是爱国老人马相伯(1840—1939)的年谱,作者为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马相伯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爱国者,震旦公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等多所著名高校的创始人之一,至今尚无学术性的年谱,本书可谓是填补空白的创新之作。
同时本书又是一部具有规范性的学术研究专著。本书依据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全面考察了马相伯的著作、演讲记录,以及与其相关的档案、报刊、回忆录等,在此基础上,对马相伯生平进行了详细考证,全面反映马相伯在教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活动和贡献,为避免片面化并适当补充背景说明,作者还设置了“谱前之年”“谱后之年”,是谱主一生行迹展开的大时代得到了全景式的展现,帮助读者理解谱主一生奋斗的历史意义。
李天纲教授坚持唯物史观,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对马相伯一生行迹作了严密的考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今年正值复旦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本书的出版对于发扬马相伯老人的爱国精神和提倡教育的科学精神,都具有重要意义。
| 作者简介 |
李天纲,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思想文化史专业,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宗教、中西文化交流和上海文化历史 著有 《年代记忆:中国近代意识的形塑》(2023)、《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 (2017)、《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1998,2019)、 《人文上海》(2004)等: 共同主编 《徐光启全集》 (2011),编辑《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相伯卷》(2014)、编校《马相伯集》(1996)等。
| 前言 |
马相伯是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首任校长,近代中国一位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二十多年中,马相伯从一个少有人知的“教育家”,被追认为“大师的大师”。确实,梁启超、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复、胡仁源、黄炎培、穆湘玥、项骧、李叔同等大师级人物,都推崇马相伯,认其作老师;戊戌变法时,自命“素王”的康有为来上海,曾暗中请教过前辈马相伯;辛亥革命后,“革命文豪”章太炎和马相伯老人为伍,两人的学问路径虽有不同,却能相互赞赏,力推共和主张;还有,抗战高潮中的爱国会“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为宣传抗日,公开表示“唯公马首是瞻”。经过几次文集编辑,多次会议研讨,马相伯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回到思想研究界的视野中,获得应有的地位。
马相伯(1840—1939),原籍江苏丹阳,生于丹徒一个天主教家庭。1851年冬,从家乡到上海,进入徐汇公学学习。1862年春,从徐汇公学毕业后,升入耶稣会修院;1864年夏,加入耶稣会;1871年,从神学院毕业后晋铎为神父,负责徐汇公学教务;1876年秋,因与教会龃龉,断然离开徐家汇。马相伯在36岁之前,接受了完整的神职训练,掌握了神学、哲学和科学等领域的全面知识,这在19世纪江南,甚至整个中国,可称是绝无仅有。徐家汇是一个国际天主教社区,神父来自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英国和美国,自幼浸染其中的马相伯未曾出国,就学会了七门外语。加之他在家乡私塾开蒙,公学中又请他兼作儒家“经学”教习,故而中西文学在同光年间均为一流。
马相伯离开了徐家汇后,投身上海的洋务运动,协助其弟马建忠(1845—1900),在李鸿章幕府中办事。他们借助大哥马建勋(1835—1882)在上海商界建立的关系,与其昌、怡和等洋行有交往,帮助李鸿章开办、改组和整顿轮船招商局,参与谋划和管理一系列洋务新局。马氏三兄弟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仅有马建忠作为“早期改良派”被提及。马相伯(建常)的早年事迹几被淹没,因他晚年创建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并在1930年代发起抗战宣传活动而为人铭记。至于马建勋作为驻沪淮军的粮台,我们连像杭州胡雪岩那样的民间传说都没有,至今也就挖出不多的几条记载,不足以描述他完整的人生。
1876年底,马相伯离开上海,入山东布政司余紫藩幕府,任职于潍县滦口机械局;1879年,马相伯离开山东,协助留学回国的马建忠处理洋务和外交;1882年,马相伯与黎庶昌等人出使日本,担任驻神户领事;1883年,马建忠成功处理朝鲜“壬午兵变”后,不暇常驻,由马相伯代替,担任朝鲜国王改革顾问;1884年,马建忠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马相伯回到上海帮助其清理账目,整顿局务;同年,中法开战,为防法军攻击招商局海轮,马氏兄弟将局产过户到美商其昌洋行名下。此举引发轩然大波,被全国舆论指为“汉奸”,一年后则不攻自破;1887年,马相伯代表李鸿章赴美借款,筹建华美银行,因受总理衙门阻挠,无功而返;此后,马相伯回到上海,生活情况不明,直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马氏兄弟重新出现在重大外交场合,参与《马关条约》谈判,又一次代李鸿章受过被污。
1896年以后,马相伯在上海露面的场合越来越多。作为洋务老前辈,马氏兄弟受年轻一辈的维新人士推崇。梁启超来上海办《时务报》,听了严复的劝告,向马氏学拉丁文。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有意请马相伯出山主持中央翻译局。此后,就是在1902年南洋公学学潮后创办震旦,再办复旦,参与筹建江苏学务总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马相伯积极参与,甚而参与组织江浙联军,投身镇、宁前线。南京光复后,他担任府尹,组织仪仗,迎临时大总统孙文入城;1912年,他被袁世凯相中,以旅朝旧师、民国功勋的身份,出任总统府高等政治顾问;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期间,他以参议员身份,主持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筹建最高学术机构“函夏考文苑”,惜以失败告终。滞留北京多年,马相伯于1919年“八十诞辰”之际退休回上海,再次息影徐家汇。20世纪20年代,本应颐养天年的马相伯回归教会,翻译《圣经》,整理文稿,口授和撰写回忆录,从事天主教会本土化建设,却仍然受蔡元培、黄炎培、于右任等旧学生们的邀请,从事众多文化、教育和政治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马相伯与章太炎等沪上名人联名呼吁全民抗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马相伯发表演讲、组织抗战自治团体,被誉为“爱国老人”。1936年12月,国民政府由冯玉祥、于右任出面,联络了南京主教于斌,邀请马相伯移居南京大方巷,协助政府动员抗战。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马相伯被迫再次迁居,先被护送到大后方桂林,再转移到越南谅山。1939年4月7日,马相伯百龄庆典之日,中共中央发表贺电,誉之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另有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的评论,言称:“从这一百年来马相伯先生的奋斗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儿女的优秀的特质,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光明灿烂的前途。”本年11月4日,马相伯在谅山去世,完成了他百年奋斗的一生。
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家的马相伯,他有同代人,甚至比他年轻一、二代的思想家都难以比拟的重要特征,即他是最早完成“西学”启蒙的学者。当然,我们一直讨论“西学”在明末已经由利玛窦等耶稣会输入,有徐光启等儒家天主教徒“会通”吸收,形成启蒙。但是,明末“西学”在清中叶遭遇挫折,“启蒙”因此而中辍。清末新教传教士重新译介“西学”,大部分华人学者对之完全陌生。同治、光绪年间的“变法”,堪以此学相称的学者,严复已是先驱,而康、梁、孙、章,都在戊戌时期“恶补”。晚至“新文化运动”倡导“西学”,号召“启蒙”的领袖人物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都未达到马相伯那样的西学造诣。当时学者论“西学”,“严、马、辜、伍”并称。以欧洲古典哲学、基督教神学和近代科学造诣论,马氏兄弟的“西学”在严复之上,而辜鸿铭、伍廷芳仅在文学、法学上擅长。查证表明,当梁启超表示要恶补“西学”时,严复向他推荐了马氏兄弟,建议他们从拉丁文学起,打好古典哲学基础,全面理解西方文明。
马相伯作为一位教育家,其成就卓著确凿无疑。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1905年再办复旦公学,都是自任校长,亲自授课,两所学校或平顺,或艰难,都成为办学质量很高的现代大学。1912年,民国初建,北京大学改革惟艰,校长任命难产。马相伯在上海办学有成,被推荐代理校长数月,曾想有一番作为,遇学潮而退。1924年,马相伯和英敛之一起,上书教宗要求帮助在北京创办一所天主教大学,获得批准,此即北京辅仁大学。马相伯在这四所著名大学的校史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痕迹,都表明他在晚年开始从事的高等教育事业是非常成功的。他为震旦、复旦提出的“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的办学理念,还有他在学潮期间要求学生“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的良苦教诲,都是给后人留下的精神遗产。此外,马相伯与张謇的江苏教育会、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蔡元培支持、任鸿隽主持的中国科学社都有密切关系,或任董事监理,或以演说为鼓励。他的一些中肯意见,在中国近代科学初期建立时也留下了印记。
马相伯离开教会期间,一直从事“洋务”,关心并参与国家大事。如果我们因此称之为政治家的话,那他显然是很不成功的一位。他自己深知这一点,故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悲凉地说道:“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1908年,马相伯受梁启超邀请,担任立宪团体政闻社总务员(社长),兴冲冲地提了“神我宪政论”政体主张,还建议了“忠实、忍耐、博爱”的民族道德。然而,他收到的却是清廷的查封,立宪派的利用和推诿,革命派的误解和攻击。以马相伯不与人争的性格,他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轨道,做一些个人力所能及的事情,不问政事多年。此后,他这种游离于出世修行和入世从政之间的摇摆态度,让他在古稀之年参加了辛亥革命,折冲权贵;随后又去了北京,在总统府担任要职,试图扭转乾坤。他亟愿为中华民国制定一部可用的“约法”,却在虚耗了多年努力之后,一夜之间回到了帝制。于是,一无所获地回到徐家汇,继续其译读《圣经》的书斋生涯。
马相伯还有一个殊为重要的身份向度,就是有始有终、伴随他一生的天主教徒身份。丹阳马家是明清时期入教的“老教友”,马相伯出生时便有洗名“若瑟”。他12岁来上海入学的徐汇公学是一所同时培养朝廷科举和本地传教人才的学校,沿袭徐光启时代“会通”中西文化的实践,既学习法文、拉丁文,又练习“四书”和八股文。1876年,马相伯脱离教会,投身洋务运动,他的才干就是徐汇公学赋予的中西会通的活动能力。1896年,在事业上经历了一连串挫折之后,马相伯决定回到教会。他的做法就是在一段“避静”(retreat)之后,搬离市区,回到徐家汇土山湾独居。马相伯在这期间的心路历程到底怎样,有哪些个人和家庭的因素促成这个转变,目前只有家族和教会间的一些传说,还没有查到关键的资料能加以完整说明。马相伯和教会的复杂关系,也有待巴黎、梵蒂冈的档案资料解密,才能完全说明。
编写《马相伯年谱长编》,是研究马相伯的基础工作,而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详尽可靠的年谱可以援引。1938年,马相伯将届百龄,已称人瑞,身边“小友”张若谷编了一部《马相伯先生年谱》,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前,很多记者、作家和学者都来采访马相伯,志愿记录“爱国老人”不平凡的生平,积有钱智修《马相伯先生九十八岁年谱》(《中央日报》,1938年5月16日)、徐景贤《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1933年4月)、王瑞霖《一日一谈》(新城书局,1936年2月26日)、陈乐素《相老人八十年之经过谈》(《人文月刊》,1930年、1931年)、刘成禺《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逸经》,1937年6月、7月)、凌其翰《九三老人马相伯语录》(《申报》,1932年5月、6月)、凌其翰《六十年来之上海》(《申报》,1932年4月30日)等。这些简单的年谱和传记,是在马相伯生前制作的,大部分都经过传主的核实,非常珍贵,令笔者获益良多。
不知什么原因,马相伯没有完成自己文集的编辑和出版,也没有像康、梁、孙、章那样自订年谱。如上提及的这些年谱传记资料,是我们当年研究马相伯生平的主要参考。深度追究马相伯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密切关系,我们发现《一日一谈》中的晚年回忆都是真实的。老人以幽默、诙谐口吻讲述的故事相当关键,且都有事实依据。谈话中对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的评价,非常中肯,很是传神,极具价值。但是,这些口述都是在马相伯九旬之后做的,毕竟常有记忆偏差,有时候会差上一两年。因此,为马相伯编订一本详尽而可靠的年谱,是不得不做的基础工作。海峡对岸,方豪先生对年谱编订最为执着。方豪最早致力于马相伯研究,马老刚去世,方豪就综合各家所述,编制了《马相伯先生在教事迹年表》(《益世报》,1939年11月12日)。1948年,方豪根据他在南京获得的一些手稿,书籍首尾的序跋,还有报章、杂志上的刊文,以及亲友、家属收藏的书信,编辑出版了《马相伯先生文集》(北平:上智编译馆)。方豪到台湾后,限于收藏条件没有更多收获,但他基于长期的积累,完成了《马相伯先生年谱新编》(李东华编:《方豪晚年论文辑》,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10年)。《马相伯集》点击卡片,即可购买
1986年12月,朱维铮老师受香港三联书店邀请执行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名誉主编钱锺书先生提议新编《马氏兄弟文集》。朱老师对钱先生的建议深以为然,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团队就开始研究马相伯。朱老师发起研究马相伯,还有另外一个契机,就是1987年开始的与多伦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许美德教授的合作项目“马相伯与震旦大学研究”。在这两个项目中,笔者负责收集马氏兄弟资料,研究马相伯与上海天主教的关系,并因此申请到亨利·鲁斯基金会的资助,1991年到1992年到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一年。三联书店的学术名著丛书首批十种因故迁延,十年后方才出版。原定列入丛书计划第二批的《马相伯集》(朱维铮主编,李天纲、陆永玲、廖梅编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遂单独出版,其篇幅已经大大超过了方豪先生的收集。此后的十多年里,朱老师在很多课题领域开拓,却一直关注马相伯研究,他为《马相伯传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撰写的《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 百岁政治家马相伯》,理清了马相伯与近代政治风云的关系。朱老师嘱咐我们继续研究马相伯,进一步考证清楚马相伯的生平事迹,做一部详尽的《马相伯年谱长编》,之后还要努力下去,设法编成一部《马相伯全集》。
2005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成立《大师》剧组,遴选近代中国一百位“大师”级的学者进行拍摄。经我们提议,编导王韧和他的团队将《马相伯》作为第一集作品投拍,由朱老师顾问辅导,笔者拟定了脚本初稿。《马相伯》一经播出,马相伯的政治、教育和信仰经历遂为愈多的观众了解。不少事件得以正本清源,各界反响热烈,以致后来有了马相伯乃“大师的大师”的说法流传。如今,朱老师去世已经多年,《马相伯年谱长编》才刚刚做完,虽有这份初步的成果,但内心却存有不少遗憾。
| 后记 |
编辑《马相伯年谱长编》和《马相伯全集》虽然是个人自定项目,但是得到了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徐家汇街道文化科、徐家汇历史文化研究会、上海志德马相伯中外文化促进中心、丹阳市马相伯文化研究会、丹阳市教育局马相伯基金会的长期支持。在此项目完成之际,笔者对区文化局宋浩杰、欧小川副局长,街道文化科刘道恒主任,志德中心马天若理事长,马相伯研究会虞瑞泰会长表示衷心的感谢。2014年,区文化局和街道文化科合共拨付5万元支持资料收集,得以启动此项研究。2024年,《马相伯年谱长编》先期完成,筹备出版,徐家汇街道又资助了5万元。特此鸣谢以上机构,更加铭记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
马相伯是复旦大学的创办人,复旦学者系统研究马相伯是由已故朱维铮先生开始的。1986年,笔者当年作为助手参与朱老师组织的《马氏兄弟文集》、马相伯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项目,至1996年《马相伯集》、2005年《马相伯传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告一段落。此后,随着徐家汇文化价值的深入发掘,马相伯纪念活动的经常举办,朱老师益发觉得此课题之重要,他吩咐要把此研究做下去,笔者遂承诺编订《马相伯全集》和《马相伯年谱长编》。值此项目将近完成之际,对朱老师嘱托和信任深表感谢。
项目执行期间,徐家汇历史文化研究会(首任理事长朱维铮,继任李天纲)、马相伯中外文化促进中心(理事长马天若)、丹阳市马相伯文化研究会(会长虞瑞泰)和马相伯基金会多次办会,共同研讨。“马研”同道们的工作热情,纯粹出乎对于马相伯事迹的喜爱。出钱出力,出智力出资源,真诚友善的氛围鼓励起笔者信心,坚持从事。在中国近代的百年动荡中,马相伯获龄百年,世人羡之为“人瑞”、“期颐叟”,誉之为“百岁爱国老人”,古今学问兼中外,门生故吏遍天下。研究马相伯生平事迹,从一开始就得到马老家属的理解和支持。1987年,马相伯孙女玉章老人接受我们的采访,录得珍贵口述史料。此后,曾孙女马百龄、玄孙马天若都经常碰面,结成友好。他们口述的家庭事迹和家族关系,帮助编辑了《马相伯年谱长编》。编辑过程中,历年结识了项骧族裔项宇、陈垣后裔陈智超、张焕伦后裔张济顺、蔡元培族裔蔡建国、黄炎培后裔黄方毅、张謇族裔张光武、冯玉祥后裔冯丹龙、李烈钧后裔李季平等。他们或提供文献史料,或告知家族轶事,亦从不同侧面帮助笔者了解相关情况。
马相伯除了自1876年至1896年这一段曾离开教会,从事洋务活动外,他一生都在教会生活,在徐家汇、土山湾留下众多印迹。年谱编辑中,来自教会人士的帮助也必须提到。1993年,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所长马爱德(Edward Malatesta,已故)神父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代为查到档案并提供,解决了马相伯离开教会的原因、日期和影响等重大问题。曾在少年时期见过马相伯的金鲁贤主教、沈保义先生接受访谈,口述资料,并多次在会议上下表示不暇分身,故而鼓励复旦学者做好马相伯和徐光启研究。多年来,上海教区光启社社长陈瑞奇神父、田愿想总编辑,佘山修院院长蓝晓鹏神父,修院马爱德图书馆馆员刘强神父,北京教区上智编译馆馆长赵建敏神父、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谭立铸秘书长都开门接待,热情答复,为复旦学者研究马相伯与教会关系提供了多种方便。
2021年秋季学期,笔者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任访问学者,期间集中精力利用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数据库,在民国收报刊、杂志和书籍中查到大量马相伯著述、演说信息,令年谱内容大为丰富。为此,要特地感谢北大文研院邓小南、渠敬东、韩笑等教授的邀请和安排。在京期间,刘梦溪、袁明、李孝聪、李零、陆扬、张志刚、王宗昱、孙尚扬、李四龙、程乐松、郑开、吴飞、王颂、何建明、李雪涛、张雪松等教授指点门径,踏访古迹,刊发论文,令访问成果丰富圆满。孟繁之、张鹿、何成军、谭徐峰、陈卓等京中朋友们提供了资料和线索,找到马相伯、陈垣在京活动的地点多处,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杨熙楠总监,天主教澳门教区刘伟杰秘书长,米兰天主教大学历史系乔万里(Agostino Gorvagnoli)、竺易安(Elisa Giunipero)教授,罗马传信部大学韩铎博士帮助提供境外咨询,召集会议,接待访问,历年来为复旦学者的马相伯、徐光启研究落实方案,提供方便。刘伟杰秘书长还无私地将自己因博士论文写作收集的马相伯资料,附加考证,无偿提供给笔者。
感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刘平、朱晓红教授,历史学系高晞、司佳(已故)、章可教授,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王启元副研究员,档案馆钱益民研究馆员,文史研究院董少新教授,研究生院任宏博士,宗教学系施亚霓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晏可佳、李强研究员,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徐锦华、周仁伟主任,文献中心黄显功、张伟(已故)、陈建华、梁颖研究馆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任雅君编辑,上海大学历史系肖清和、王皓教授,上海市委统战部研究室张化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赵建海、朱达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卓新平、任延黎(已故)、王美秀、刘国鹏、周伟驰、唐晓峰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刘贤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李兰芬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邱江宁、蒋硕教授,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玉琴教授,山东大学历史学系刘家峰教授,山西大学历史学系赵中亚教授,丹阳市马相伯研究会卢政、吉育斌先生。他们在本年谱编撰过程中有求必应,提供了诸多咨询意见和资料。
感谢徐汇区土山湾博物馆(暨马相伯故居)陈耀王名誉馆长、冯志浩、朱春峰、金志红、张晓依、张婕馆员,徐光启纪念馆寿颖之馆长,徐家汇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傅亮先生、袁洁女士,徐家汇主教堂杨磊教友,徐汇中学郑斌老师,徐家汇气象台邬锐研究员、博物馆赵国新馆长。徐汇区文化局自2003年起修复地区文物场、馆、点,创建徐家汇源景区City Walk(文物径)红线旅游系列。在宋浩杰局长邀请复旦等校学者一起发掘考证文献记载的时候,我们一群学者对于马相伯在徐家汇、土山湾生活学习的经历也就越来越清晰,年谱的编撰也变得精细。4A级景区“徐家汇源”(2012)文物系列的修复和开发,正和《马相伯年谱长编》的编撰过程同步,研究与行走,合作时互通互补。顺着马相伯的足迹,问百年事,行千里路,查万卷书,《马相伯年谱长编》的编撰自是艰难,也还是很愉快。
感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领导对此项目的支持,孙向晨、张双利院长、袁新书记多次关心编撰工作。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历届领导多年来对于马相伯研究出版的长期支持。《马相伯年谱长编》出版得到严峰董事长、王卫东总编辑的亲自关心,责任编辑顾雷在约稿、立项、审稿和申请资助阶段花费大量精力,出力最多,在此特表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