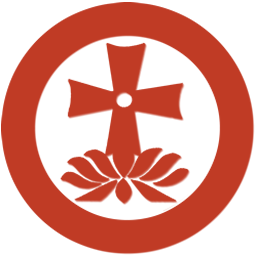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1年第17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134
张志刚(北京大学)
摘要:中国著名基督教哲学家、神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赵紫宸(T. C. Chao,1888-1979),堪称倡导“基督教中国化”的思想先驱。关于赵紫宸所阐发的“中国化基督教”思想,虽然以往海内外学者早就有所关注,但尚未加以系统化的专题研究。本文则试图在以往研讨的基础上深化一层,即聚焦赵紫宸“中国化基督教”思想的问题意识,深究其思想的逻辑进路,发掘其思想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西方基督教、基督教本真、中国文化、中国民族、中国化的基督教
DOI: 10.29635/JRCC.202112_(17).0001
赵紫宸(T. C. Chao,1888-1979)是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中国基督教思想家之一,他不仅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基督教哲学家、神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而且堪称倡导“基督教中国化”的思想先驱。关于赵紫宸所尝试阐发的“基督教本色化或中国化”思想,虽然以往海内外并教内外学者早就有所关注、有所评论,但尚未加以系统化、深入性的专题研究。本文则试图在以往研讨的基础上深化一层,这就是聚焦赵紫宸“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问题意识,深究其思想的逻辑进路,发掘其思想的时代意义。
据现有收集原作最全的《赵紫宸文集》(五卷本)来看,赵紫宸关于“基督教本色化或中国化”的思考,主要集中于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至三十年代末,主要论著包括《今日中国的宗教思想和生活》(1926)、《研究儒家属于宗教部分的材料》(1926)、《中国人的教会意识》(1926)、《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1926)、《信基督的国民》(1927)、《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1927)、《我对于创造中国基督教会的几个意见》(1927)、《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927)、《我对于创造中国基督教会的几个意见》(1927)、《基督徒对于日本侵占中国国土应当持什么态度》(1931)、《基督教与中国的心理建设》(1932)、《一条窄而长的路》(1934)、《中国民族与基督教》(1935)、《这正是我们献身的时候》(1936)、《“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936)、《学仁》(1936)、《新时代的基督教信仰》(1940)等等。
依笔者之见,上列近20种论著里,最能反映赵紫宸探索足迹、最有思想创树、也最有代表性者,要数时隔八年所撰、标题醒目的两篇文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与基督教》。所以,本文基于着重诠释这两篇代表作,广为参考赵紫宸及同时期中国教会学者的其他相关论著,并按忠实于一手文献的学术规范,从中吸取“西方基督教”、“基督教本真”、“中国文化”、“中国民族”、“中国化的基督教”等关键词,用以还原与评论赵紫宸“中国化基督教”思想的问题意识、逻辑进路与时代意义等。
一、本色问题:为什么要融入中国文化?
为什么基督教要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呢?这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927)一文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赵紫宸对此问题的思考,是在“本色化教会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双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他一提笔就指出,早在“反基督教的旗帜”出现之前,中国教会内部就兴起了“本色教会的声浪”。此声一起,“中国化的基督教”等思想便随即回旋于“我国信徒的心胸”。这种思想的内容就是“两种根本的承认”:一是,中国基督徒清澈地承认,基督教虽然层层包藏于“西方教会的仪式、教义、组织、建筑”之中而几乎不见其真面目,却有“一个永不磨灭的宗教本真”;二是,中国基督徒干脆地承认,中国传统文化虽对(现代自然)科学无所贡献,却有“精神生活方面的遗传与指点”。正是基于“这两种根本承认”,中国基督徒才觉悟到“基督教本真”与“中国文化精神遗传”相融会贯通的必要性。这也就是说,基督教若能真正“祛除西方的重重茧缚,加以中国的精神阐发”,必能被中国人所了解、所接纳。
我们是中国人,活在中国的环境里,然而我们亦吸收世界的文化与基督教,亦曾在中国的思想境界里优游。一到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宗教信仰时,无论我们用甚么方式,我们所发挥的总要与各国的基督教有不同的仪型。我们自发的基督教生活在根本上原是世界的基督教,在殊异方面即是中国的基督教。“本色教会”四个字,不过是四个字罢了。好像一个活泼的人要穿一件衣服。他在西方穿西服,就是洋人;在中国穿华服,就是华人;在本国穿本国服,就是“本色”人。[[1]]
若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赵紫宸认为,决不能用“机械的方法”,“中国化的基督教”也并非“一朝一夕所能产生的”。但尽管如此,中国基督教思想家眼下必需思考两个两点:一是“基督教的本真何在”?一是中国文化具有哪些“势力倾向”可与基督教融会贯通?这里所谓“中国文化的势力倾向”,就是指那些依然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态度”的精神遗传,这主要体现为中国人对“自然、伦理、艺术、神秘经验”四方面的态度。今天看来,赵紫宸对前三方面的分析论述仍不失理论参考价值,下面将其论证要点概括为“中国文化的自然观念、伦理倾向、艺术倾向”。
1、中国文化的自然观念
中国人对“自然”持有特殊的态度,这可谓中国文化所具有的“首要势力倾向”。在中国思想史上,“自然与人”两个观念非常融和。《易经》的根本原理之一就是,自然与人只有一理,物理伦理,本无分别;人在自然里见人道,在人生里见天道;人的最高生活就是“道法自然”,“机械与自由”、“心与物”并没有截然对立、两不相容的界别。《易经》谓“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大人能知天合天。“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君子能自强,是有自由的,人的自由与自然法则并不冲突。
西方人的自然观念则与上述中国思想相反。西方人推求“物理”,将万物视为“客观的机械系统”,而人外在于物以免“主观的危险”,物外在于人以成“抽象的观念”。这样一来,“人与自然”便成为“敌对关系”;“物的机械”不能解释“人的自由”,于是有人主张“定命之说”;“人的自由”在“抽象的思想系统”里没有地位,于是主张“自由之说”的人无法统一思想。
通过上述观念比较,赵紫宸认为,我国“天人一贯之说”,实为我国的根本思想。自然与人,其道一贯。如《道德经》三七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庄子·齐物论》曰:“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非自成己而己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但与此同时,赵紫宸指出,“中国的伟大在此,中国的衰弱亦在此”。“亲近自然”是我国人的特性,知人知天,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对我国人来说是一回事。可是,我国的思想只能暗示“自然的道理”就是“人的道理”,而没有清楚地表明“自然暨天”的实在性,天与人一样也是有“人格”的。因而,中国古代思想家一方面感悟到天地间包藏“道德的本原”,另一方面又觉得天地并不表显“人格”;久而久之,“原本活泼的道”在宋儒那里变成了“静止寂息的理”,并且要人做到“无我”,放弃“自己的人格”,方能真正“合德于天地”。以下是赵紫宸所做比较的结论:
我国的思想偏于人生方面,故所用的方法,直验直觉,常近于宗教的方法。基督教要与中国文化发生关系,在此知识方法一端大有相似之点。至于我国的思想偏于法自然,甚致于绝圣弃智,至公无我,或固为儒或入于道,或流于佛,皆与基督教的根本信仰不同。法自然故人的高点——峻极于天处——即是无心无情,即是无我。基督教不然,耶稣教人乃以人信仰中所组织所见示的至高上帝——人格——为高点,所以说“你们应当纯全像你在天的父一样完全”。这种思想到中国的文化境界里不能不使其自身发生变化,亦不能不使中国固有的文化发生变化。至其变化的趋向如何,全在吾基督教的知识与经验不能不达到高深悠远的程度。[[2]]
2、中国文化的伦理倾向
人之为人,要有“做人的道理”。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所谓“仁者人也”,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人与人相处,推本便是“孝”,尽己便是“忠”,及人便是“恕”。“礼、智、信、廉、让、勇敢”等,皆是“仁者”与人相处的种种美德;所谓“孝、保本返始、慎终追远”等,均在浑然一德。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族社会,故其伦理也是家族性伦理,虽然不免守旧,却不失为人性至意,足以巩固社会基础。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伦理的实体是“仁”,“仁”的根本是“孝悌”。胡适把中国宗教称为“孝的宗教”,赵紫宸则进而认为,中国伦理是“孝的伦理”,伦理之极致,便成为宗教;孝是道德,旨在为人;孝是宗教,旨在报本。
那么,在中国文化与社会处境下,基督教何以能与“孝道伦理”融会贯通,且能做出什么贡献呢?在赵紫宸看来,耶稣的深刻经验及其重要教训,就是作为“上帝之子”,为了爱人而献身十字架。这种生命体验及其人生教益,是与中国的“孝理孝教”颇为一致的。因而,从今以后,中国基督教若对中国文化有所贡献,一方面必须推广“孝义”,使人们仰见“天父上帝”,以深邃的宗教经验来巩固孝道伦理基础;一方面则应使人作为“上帝的子女”而获得个性解放,摆脱旧制度束缚,并保持民族性精神,在新社会中实现“人人平等的弟兄主义”。当然,若在这方面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也要看中国基督徒能否深切地了解、鉴赏与创化我国的伦理传统;假若不够深切,只能随波逐流而已。
3、中国文化的艺术倾向
宗教是“弥漫融洽的生命”,绝非言词所能尽述,也绝非任何方式可以尽达。因而,作为生命的宗教,并非像近代思想家以为的那样,仅以伦理行为足以表显,或以社会心理足以说明,或以音像美艺足以取代。既然宗教并非一种方式所能表显,故必运用“象征”,象征手法则必借重美术。赵紫宸进一步指出,凡有宗教,必有仪式、建筑、音乐、绘画、文章等,借以传递宗教生活的丰富多彩性。自晋六朝隋唐以来,道佛两教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尤以佛教在庙宇绘画、宗教音乐等方面有显赫贡献。由此可以想见,信仰者因胸怀深远幽邈的宗教经验,便借助各种艺术形式,像造庙宇、建仪节、创音乐、作诗歌、立佛像、图诸天等,象征性地表达其种种宗教经验。换言之,没有宗教经验,决不会有庙观、佛像等物;宗教经验不易表明,宗教美术就是宗教言语。
作为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与思想家,赵紫宸说到这里大发感慨:我们中国的美术发自“自然的经验”,最能表达心灵感触。譬如,淡墨山水,试问这件作品或为雄浑,或为悠远,或为沉著,来自哪种理论?又如,王维诗句,“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假若囿于字面解释,岂不是讲一个人在山里疯癫似地举头独看槿树枝,在松树底下采了些带露的葵实来充作野餐,竹树里有明月照亮他自己而已?这还有什么意味、什么神情?意味神情,皆在言外。所以,陶渊明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真意乃在不言之言。若有人问:李白诗句“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是怎么一回事?恐怕无言可答,只能说“这不是什么一回事”。赵紫宸就此小结:“中国的诗书建筑特别注重传神,特别富有与宗教相类的意义。假使基督教要在中国人心血里流通,她必要在美艺上有贡献。”[[3]]
二、十年之问:基督教在中国有何前途?
1926年秋,赵紫宸曾写过一篇《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按他那时说法:“基督教不分中西内外,不有种族家园。因此各国各族的基督教即系我国的基督教,于是则曰,基督已久矣……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光明黑暗,全视基督教中为导师为领袖的人,在于今日,不能不发扬基督精神以为断。”[[4]]
然而,对照研读赵紫宸发表于1935年秋的《中国民族与基督教》,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作者的如下自我反省:近十年来,朋友们往往质问:基督教在中国有何前途?所有的议论,或失之“过于乐观”,或失之“过于悲观”。二十多年前,我初入教,锐意奋进,竟以私意论断,不出三十年中国必有大众皈依基督教;如今每觉少年之时,只重义气,只凭主观,宗教热忱有余,历史眼光与科学态度全无。因而,此文试图以历史眼光与科学头脑,再思“十年之问”。[[5]]
统观中国历来宗教的发展演变,便可推测基督教在中国前途,试问基督教在中国能否根深蒂固?为了探究这一问题,赵紫宸在该文里较为全面地勾勒了“儒、道、释”三教的兴衰过程,其中尤以对“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分析”令人眼光一亮,可谓提出了“外来宗教中国化比较研究”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的主要论点如下。
赵紫宸首先指出,如果中国人需要宗教的话,总须中国人自己去求。“求”有三端:“求诸行、求诸源、求诸文”。佛教传入中国,在这三端皆有伟大成绩。例如,晋末高僧慧远,自别于鸠罗什一派而创立佛教南宗。那时的士大夫谈玄虚,崇老庄,放浪不检,生活颓废,而慧远却能超脱俗尘,严持戒律,深入庐山,住大林寺,成为整饬力行的一世大师。这是“求诸行的显示”。再如,法显玄奘及上百僧人,冒万险,辟千难,登葱岭,度雪山,无路中开路,无生中得生,或死于去路,或死于归程,或死于异域,或死于种种险阻、疾病、贫困、饥寒等,就是要到发源地求经求教。这是“求诸源的显示”。至于“求诸文”,佛教的伟绩更值得一提。译经一事,起先都是月支、安息、于阗、天竺等外国人做的,后来中国人自己精谙梵文,且深识佛学的环境与背景,深知中国的文学与历史,便自相传译,即有玄奘三藏、义净三藏等“印印皆同,声声不别”的翻译。除了玄奘和义净,佛经译者几乎指不胜屈。这是“求诸文的显示”。正是着眼上述比较视野与“求之三端”,赵紫宸深刻反省了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传入的复杂历史背景及其不良社会后果。这一长段“教内思想家的自我反省”,当年堪称“发前人之未发”,值得不惜篇幅,完整照录如下:
基督教与佛教不同;中国人不曾去求基督教,因为中国人不曾感觉到去求的需要。西国人来传教,是西国人自己内心中迫不得已的遣使;他们心中受命于天,只要打开中国的门路,即不问其所凭借的威力都从哪里来。于是乎,传教有条约,有西洋的政治力作后盾。我友张伯怀说:“十九世纪之初,基督教的宣传是一种侵略行为。西国的传教士们把自己所服膺的宗教,用他们国家的武力为后盾,强制的在中国宣传。至于中国人方面是否欢迎,基督教对于中国人生到底有何贡献,并未加以仔细的考虑。二十世纪的开始,就是庚子之乱。从那时候起(这一点是错的,因为在此以前中国人就是反基督教的),中国人拒绝基督教的思想,在在潜滋暗长……大有‘此害不除,中原不安’的愤慨。结果是民国十一年非教大同盟的组织,和联俄容共以后的反基督教宣传与设施。”(见鲁铎七卷一页)基督教既不仗本身的灵光,而仗外国势力以为播散之法,则中国的信徒当然不免于仗洋势,以自卫,以欺人,而中国的人士当然不能不有人民教民的区分,视教民为汉奸,为洋奴,弄得“火烧昆岗,玉石俱焚”。中国人信了基督教,既有作洋奴汉奸的嫌疑,则其所信的国教,当然不能深入而浸润中国的文化。基督教与中国民族的扞格不入,这未始不是一个甚为不幸的理由。[[6]]
赵紫宸接着指出,有人以为“基督教不能融入中国,是因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龃龉”,其理由有如下种种:中国人祭祖,基督教嫉视祭祖;中国人重男轻女,男子可以娶妾,基督教则坚持一夫一夫制,绝不容让;中国人惟上是从,基督教则主张平民主义;中国方兴国家思想,基督教则欲破除国家畛域;中国人注重过则不惮改,基督教则强调人不能自救,须忏悔罪过,邀上帝垂援;中国人喜好悠游自得,基督教则以自苦为极;中国人大都不信人格神,基督教则以人格神为中心信仰;中国人不善于组织,基督教则倾力教会及其典章、制度、神学等。这样一些言论,初闻如甚辟警,细思大谬不然。
佛教初传时与中国民族心理不合,何以兴?因其有真际,有内力。若与佛教相比,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的冲突之处其实更少,因为中国人重现世、重人生,基督教在这两方面或可发挥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中国人在生活与思想上已不再重男轻女、尊君抑民,而是历代有识之士所倡导的“积极为公的牺牲精神”。就此而言,基督教并不反对现代国家意识,且能以“一视同仁、人人平等”心志,助力中国文化保持其“天下为公、天下一家”理想;基督教所主张的“博爱”精神,也就是《论语》里所讲“泛爱众”、“博施济众”的意思,为什么基督教必被中国文化所排斥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根本差异仅在于,是否相信“人格神”。然而,神由人显,人能显神,即可配天,圣人配天,本来也是中国道理。假若基督教能有科学的态度、宗教的精神、信仰的能力,在学问上奠定善知识,在生活中彰显好行为,为民众心灵注入新精血、新生命,又岂非今日中国所迫切需要的?
与佛教发展时期相比,今日中国基督教的时代处境已显然不同了。这就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若要在现代中国得以生存发展,且要适应中国民族需要,基督教的“内部实力”又如何呢?这里所谓“内部实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指中国教会的自身建设问题。赵紫宸笔锋犀利地指出了两大现存问题:一是“人才”,近百年来,试问中国教会有何等何种人才崛起于士林?有何高才硕德堪为“教内外楷模”?新文化思潮出了一位胡适之,基督教是否有同等人才?若有的话,其号召力与影响力何如?西方传教士与教育家曾长期把持教会人材培育机权,他们似乎另有一种眼光,一边选用“贾贩走卒、庖丁书佣”来做牧师,一边则由教会学校造就政界精英,却唯独不曾训练出中国教会的思想与生活领袖。中国教会里少数几个可以宣教理、弄文字的人,大都未受过西方传教士或教会的赏识与栽培,而目前此类人数依然“置斗室而不满”。二是“组织”,中国教会形形色色的组织形式,皆为西方舶来,从神学思想、宣教方式、崇拜礼仪、教堂结构、诗歌著述等等,无不取自外洋。一旦洋钱绝,洋人归,洋式揭穿,究有何物,恐怕风流云散,瓦解冰消!
说到这里,赵紫宸回应“十年之问”:基督教在中国有何前途?在他看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将主要有赖三件事:首先,对上帝的信仰,这是一切的根本,否则世上便没有基督教。然而,在这一点上,基督徒只有信仰而没有凭据,因为所谓“宗教”原是“一种豪迈英爽的人生赌博”[[7]];若愿赌注,可以有所作为,可以通过“深刻的研究”而获得“纯精的学问”,为基督教信仰做出“中国化解释”。因而,从今以后,中国基督教须有“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宗教哲学与人生哲学”。其次,宗教是“行”(求诸行),中国基督教若要生存发展,信众的行为必须较之平常人更加高洁隽永,若不能像佛教那样涌现一辈“舍身燃指的男女人才”,基督教在中国将没有存在价值。再次,基督教能否在中国发扬光大,还须有待于世界基督教的转向与进步,即在思想上须能攀登科学梯阶,在实践上须能为人类创造新文化。总之,中国基督教既已略知自身弱点,便应自当力事革新。[[8]]
三、撷英采华:昔非曲高和寡,今非老调重弹
基于前两部分尽可能“原汁原味的原著研读”,笔者试借两个成语寓意来展开两相穿梭的思想评论:一是,昔日赵紫宸的“中国化基督教”思考并非“曲高和寡”;二是,今日我们重新梳理与诠释其思考的问题意识、逻辑进路与时代意义,也绝非“老调重弹”。
历史人物的思想评论,不可或缺历史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有一句方法论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9]]在笔者看来,这一论断尤为贴切于典型人物的思想史研究,可启发我们从“思想者最为注重的问题意识”切入,探析其思想言论是否具有代表性、前卫性、深刻性乃至重要历史意义等。
如前所述,赵紫宸关于“中国化基督教”的思考,在问题意识上初始于:为什么基督教要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这一难题又主要是在“本色化教会运动”背景下提出来的。那么,何为“本色教会”?在赵紫宸发表其代表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同一年,著名基督教史学家王治心也撰文指出:“从上述几位先生所说定义中,可以归纳出一点共同的意思来,就是:所谓本色教会者,即富有中国文化的素质,而适合于中国民族精神和心理的教会也。”这里所提“几位先生的定义”包括《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刘廷芳、赵紫宸、诚静怡、周凤等的理解。同时值得一提的是,王治心所撰该文还附有“国学入门书目表”,按“经史子集”四部,从《论语》、《孟子》、《礼经》、《诗经》、《孝经》、《周易》等,一直列到《近思录》、《传习录》、《日知录》、《思问录》、《国故论衡》等,其总数不下百部。[[10]]
由此可见,赵紫宸所思考“为什么基督教要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不可不谓当年中国基督教会本色化运动所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如果再来比较一下同时期教内学者所发表的思想言论,则可以进一步肯定:赵紫宸就此问题所做的深入思考,显然并非一己之见或曲高和寡,而是不乏思想知音及其理论共鸣。例如,刘廷芳同年撰文指出,近五年来,基督教在中国所取得的一大进步可谓至关重要,这就是中国基督徒已有两方面的觉悟:其一,基督教是与我们中国民生与国势有密切关系的;其二,基督教必须在实际上祛除“洋教的彩色”。因此,“基督教须经过中国文化的洗礼,不是因为基督教没有中国文化不能成立,实在是因为我们个人不能脱离了文化而生存。”[[11]]再如,诚静怡来年撰文强调,“基督教会无论到什么地方对于一民族所有特殊的风俗,遗传,文化,及环境等之利用,确具有充分的适应力。这犹如我们对于衣服那样,可随时随地加以应有或弃置……这样看起来,基督教在中国,也必迟早变为中国的基督教。基督教因为具有这样的适应力,所以就成为世界宗教。”[[12]]又如,谢扶雅发表于1926年初的《本色教会问题与基督教在中国之前途》则显得更为激奋:“基督教汩没于西方帝国主义盔甲之下久矣。吾人方将液出而爬梳之,洗濯而整理之,以实现其庐山真面目,而深植于中华民族之土壤中……行乎勉哉,此殆我中华民族改造基督教之伟大使命欤!”[[13]]
以上相互印证的文献诠释表明,赵紫宸所思考的“中国化的基督教”不仅堪称“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的关键问题”,而且从根本上关乎“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问题”。据此我们可以进而理解,为什么赵紫宸时隔八年要再思“十年之问”,其论著且以鲜明的标题《中国民族与基督教》,将“中国民族”作为思考“基督教在中国有何前途”的语境前提。
这里有必要先对“中国民族”一词释义。据近现代史专家黄兴涛考释,最早使用“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并主张“中国各民族融合一体”的近现代思想家是梁启超(1873-1929)。早在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就萌发了“对外抵制外族侵略,对内实现族类团结”的中国民族意识。在1901年所作《中国史叙论》里,梁启超多次固定使用“中国民族”一词;同年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里,则并列使用“中国民族”与“中华民族”两词。20世纪初期,在中国各民族总体意义上使用“中国民族”一词,已被我国知识界普遍接受,这一具有时代标志性意义的新名词,乃是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萌发在语言词汇上的最初反映。[[14]]关于“现代中华民族意识”,亦即中华民族“现代国家意识”的形成背景,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做出明确的解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这里所用的“中华民族”一词就是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几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6个民族单位是“多元的”,中华民族是“一体的”;这里所讲的“中华民族”和“民族单位”,虽然都含有“民族”一词,但二者的层次不同,前者“中华民族”就是指“国家”。[[15]]
以上略显复杂的概念释义,可使我们充分感悟到,赵紫宸《中国民族与基督教》一文所饱含的中华民族国家意识及其再思“十年之问”的潜在用心。譬如,该文为什么要以“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基督教”的比较视野,提出“求有三端”?为什么分析这“三求”时要把“求诸行”摆在首位,而不是按一般逻辑次序先提“求诸源”与“求诸文”?为什么要借此“三求”的比较分析,着重反省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传入的复杂历史背景及其不良社会影响?要而言之,这一连串试图推进“中国化基督教”思考的问题意识,旨在呼应“中国教会前途十年之问”所积淀已久的“中华民族观念暨现代国家意识”。
例如,早在发表于1927年的《今日教会思潮之趋势》一文里,张亦镜就快言快语:中国各地教会,从英国传来的,就带有英国色彩,德国传来的,就带有德国色彩,美国传来的,就带有美国色彩;甚至教堂门大书“大英国、大德国或大美国某会礼拜堂”,有什么较大的聚会,还扯起外国的旗子;信徒中无耻者,还自称“某国某教会教民”!中国的土地上建了某国教堂,就是某国的领土!中国的人民入了某国教会,就是某国百姓!中国教会提倡本色化,就是要“去除如此种种外国色彩而换上中国的颜色”。[[16]]再如,在同年发表的《中国基督教的性质和状态》一文中,诚静怡直言不讳:基督教传入中国,是跟着西方列强的军事胜利而俱来的,因为这时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压迫之下,不得不签订不平等条约,为西方商人开辟许多商埠,这些不平等条约里,包括特别保护西方教会传教的条款,西方各国传教士们就是趁此时机而把基督教福音传入中国内地的。与此同时,西方教会又把“宗派主义”输入到中国;而“宗派主义”本来是西方教会的历史产物,现在却导致中国教会团体各行其是、分道扬镳,但我们中国人对这些门户之见并没有多达兴趣。[[17]]又如,1935年,也就是在赵紫宸发表《中国民族与基督教》的同一年,吴雷川一落笔就激情呐喊:
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在先时,只是稍有思想的人不期然而然的潜伏着这意识,现时却已发出急切的呼声,激荡全国了。不但一般知识阶级以此事相倡导,就连政府也公开的就此事唤起民众,认为治本的目标。所以现时凡是对于某种学说有所研究,或对于某种政策有所主张的人们,都要将他们所研究、所主张的提出来,贡献于这时代的国家和社会,他们都要竭尽各个人的心思才力,在这一桩绝大的工作上有份。且不问现时各个人的动机如何,将来各方面的收效如何,就凭着这风发云涌普遍的现象,已可说民族将要复兴的先兆。因此在这时候,在这地方的基督教,就不能不发生问题。这问题就是:基督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能有什么贡献?[[18]]
以上引文是吴雷川所撰《基督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能有什么贡献》的首段文字。这段开场白,可把今日读者引回到“九一八事变”之后、“一二九运动”前夕国人对抗日救亡、中华民族复兴的强烈关注。据此历史背景不难认识到,以赵紫宸、吴雷川、谢扶雅、诚静怡、刘廷芳、王治心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教会知识份子关于“十年之问”的思考,已不再限于“基督教本色化问题”,而是将“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与国家存亡、中华民族复兴密切联系起来了。
历史人物的思想评论,也不可或缺现实感。诚如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Bendetto Croce,1866-1952)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9]]这句史学方法论名言,可令人深悟历史人物思想研究的意义何在?据前述原著梳理与诠释,赵紫宸作为倡导“中国化基督教”的思想先驱,其心路历程可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意义上归结为:从“思考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会贯通”进而“反省基督教与中国民族的命运关系”。就现今研究状况而言,这一心路历程暨逻辑进路显然具有思想史典型意义与当下性启迪价值,这就是基于“文化认同”来构筑“国家认同与社会认同”。正如中国教会著名学者陈泽民评价:在20世纪初到新中国建立的漫长而艰苦的半个世纪中,赵紫宸先生坚持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必须走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和现实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道路。他留下来的丰富思想遗产,正是他作为“创建中国教会神学的先驱心声”。[[20]]最后,笔者还想交代一句,如同任何过往的思想家,赵紫宸关于“中国化基督教”的思考,无疑也有其特定的时代局限性;我们如今回顾其思想历程,不必苛求某些不足论点,而主要是为了从中撷英采华,获取启迪,继续探索。
C. Chao's thoughts on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ZHANG Zhigang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 C. Chao (1888-1979), a famous Chinese Christian philosopher, theologian, educator, and literary scholar, is a pioneer in advoca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Although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long paid attention to the thought of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expounded by T. C. Chao, it ha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studied.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deepen one layer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es, that is, to focus on the problematic consciousness of T. C. Chao's thought of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to investigate the logical progression of his thought, and to discover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thought in the times.
Keywords: Western Christianity, Authentic Christianity,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nation,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1]] 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原刊于《真理与生命》第二卷第九至十期,1927年;现载于燕京研究院编:《赵紫宸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8页。
[[2]] 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赵紫宸文集》第三卷,第274页。
[[3]] 以上关于中国文化的三大势力倾向的分析论述,详见《赵紫宸文集》第三卷,第271-276页。
[[4]] 详见赵紫宸:《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原刊于《真理与生命》第一卷第十二期,1926年;现载于燕京研究院编:《赵紫宸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30-231页。
[[5]] 赵紫宸:《中国民族与基督教》,原刊于《真理与生命》第九卷第五、六期,1935年;现载于《赵紫宸文集》第三卷,第628页。
[[6]] 赵紫宸:《中国民族与基督教》,《赵紫宸文集》第三卷,第636-637页。
[[7]] 赵紫宸在此所言“宗教”原是“一种豪迈英爽的人生赌博”,并非其个人“戏言”或“比方”,而是显然借鉴了关于宗教本质的意志论观点——“打赌说”,这种意志论观点的提出者与论证者,主要是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基督教哲学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宗教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n James,1842-1910)。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拙著《宗教学是什么》里“宗教与意志”一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 详见赵紫宸:《中国民族与基督教》,《赵紫宸文集》第三卷,第640-641页。
[[9]] 关于这一命题的具体内涵,详见[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10]] 详见王治心:《本色教会与本色著作》,原刊于《文社月刊》第一卷第六册,1926年;现收入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旅——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235页。
[[11]] 详见刘廷芳:《为本色教会研究中华民族宗教经验的一个草案》,原刊于《真理与生命》第一卷第七期,1926年;现收入《本色之旅——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第337-347页。
[[12]] 诚静怡:《中国基督教的性质和状态》,原刊于《文社月刊》第二卷第七册,1927年;现收入《本色之旅——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第269页。
[[13]] 谢扶雅:《本色教会问题与基督教在中国之前途》,原刊于《文社月刊》第一卷第四册,1926年;现收入《本色之旅——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第254-255页。
[[14]] 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0-65页。
[[15]] 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首发于《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16]] 详见张亦镜:《今日教会思潮之趋势》,原刊于《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九期,1927年;现收入《本色之旅——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第364-365页。
[[17]] 参见诚静怡:《中国基督教的性质和状态》,原刊于《文社月刊》第二卷第七册,1927年;现收入《本色之旅——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第271、274页。
[[18]] 吴雷川:《基督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能有什么贡献》,原刊于《真理与生命》第九卷第二期,1935年;现收入《本色之旅——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第62页。
[[19]] 关于这一命题的具体内涵,详见[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博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0]] 同时参见陈泽民:“为赵紫宸文集题词并代序”,载燕京研究院编:《赵紫宸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