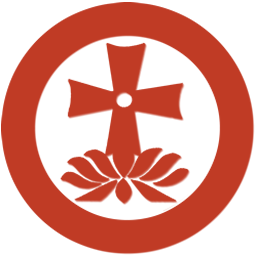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1年第17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142
张仕林(北京电影学院)
摘要: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自1904年起便开始在中央会所里放映电影,第一是为了满足青年会自身运营而进行的商业性放映,第二则是为了满足精英阶层的“健康有益的娱乐”需求和促进对青年会会员的公民教育而进行的公益性放映。中国进入局部抗战阶段,香港青年会在延续以上两种电影放映的同时,利用电影为国家救亡事业进行筹款并服务社会,通过儿童剧团的戏剧与电影活动发扬了民族精神,培养了健全的现代公民。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香港青年会与广州青年会共同组建了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并设立电影队随粤军北上并进行流动电影放映,为士兵带来精神慰藉的同时激发了军民共赴国难的爱国热情。
关键词:电影放映、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香港电影文化、抗日战争
DOI: 10.29635/JRCC.202112_(17).0009
引言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香港青年会”)[[1]]是传教士苏森奉北美协会之命于1901年成立,除了本着基督教教义“以德智体群四育服务社会,培养人格,其事工以全社会为服务对象”,[[2]]青年会的会所里还可以供会员娱乐、健身及阅读书报等。[[3]]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局部战争开始。[[4]]凭着得天独厚的殖民地背景和大量华侨聚集特征,香港成为中国争取外国支持和援助的门户和海上通道,来自世界各地的物资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驻地在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因“与内地之交通日渐隔绝”实际已停止工作,“为接洽便利起见”,一部分人随着军队迁移至长沙并设立了办事处,[[5]]但长沙也在1939年9月进入保卫战,主要人员开始逐渐向香港搬迁,上海协会领导地位“已无形中让位于香港”。[[6]]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自1907年搬入四川路会所后便开始了定期放电影的事工。张隽隽通过对《申报》中青年会电影广告的爬梳,对青年会基于经营、教育、公益、娱乐等方面的电影放映梳理后认为其电影活动不仅为青年会带来了经济收益,其世俗化色彩减少了民族主义情绪冲击。[[7]]菅原庆乃则对上海青年会非营业性电影放映的整理和分析后认为青年会“‘有益而健康’的电影活动不但开拓了新的观赏态度和娱乐方式,也促进了观影行为的现代化”。[[8]]
身处殖民地的香港青年会前期并不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下属机构,在相关文件中还与高丽青年会做了并列呈现,称为“中韩香港青年会”,直到1907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才将“香港”二字剔除。[[9]]近代以来的香港被称为“远东繁华大埠之一”[[10]],20世纪20年代电影放映事业进入发达阶段,在此期间香港青年会的电影放映是如何开始的?特别是在抗战期间,香港青年会的电影放映如何进行,对民族救亡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运动一直处于同步状态,二者还存在着同基同源的设想:救国与树人,即国家变革与个人发展相互依存,[[11]]那么香港青年会的电影放映在战争期间又是如何参与救国公民的培养?
基于香港青年会的机关刊物《香港青年》及《大公报》《申报》等刊物的爬梳,本文将尽可能地将这段被逐渐遗忘的历史进行重新叙述,填补香港电影文化中一处独特的风景,探讨抗日战争期间以基督教青年会电影放映为中心的香港与内地的多维度互动情况,梳理其电影放映活动在战时不同区域内面对不同受众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
一、精英阶层的高尚娱乐:智育与群育中的电影放映
基督教青年会虽然以社会服务和培养人格为宗旨,但必须厘清几点历史事实:第一是近代以来尽管经历了多次反基督教运动,外国教会在中国所设立的教堂却形同中国境内的第二个政府,外国的传教士与中国的官员也是按照对等职分平起平坐;[[12]]第二是民国政府长期以来便与基督教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孙中山本人就是基督徒,袁世凯虽然不信基督教也曾在民国召开国会期间吁请美国新教徒在各自的教堂内祈祷,[[13]]而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证婚人正是担任过黎元洪秘书的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14]]第三是余日章、王正廷等在青年会全国协会担任要旨的人员基本上都曾自费留学美国,[[15]]长期出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还不乏谭延闿、宋美龄、鲍恩咸、鲍庆甲、陆洁等政商文教名流。另外,基督教青年会在吸纳会员的时候虽不会对是否为基督徒身份做出确认,但加入该组织需定期缴纳一定额度的会费作为机构日常工作的经费,在民众收入水平普遍不高的近代社会,城市中下等阶层的收入大概是每个月17元左右,而城市贫民只有8.5元左右,[[16]]入会费用实际上已经阻挡了社会中的大部分民众与青年会的联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基督教青年会实质上存在着精英阶层俱乐部的特性,无论是招待青年的电影会友还是商业性放映,青年会的电影放映及其吟诗作画、体育锻炼等活动只能说是精英阶层的高尚娱乐。
香港青年会自成立起便与文化电影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如1917年香港青年会举行的新年欢叙大会上,黎民伟夫人[[17]]在活动中“给发文庀赠品”;[[18]]在1927年,鲁迅到广州大学任教后于2月份到达了香港进行交流,并在18日和19日落脚香港青年会分别做了《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两场演讲;[[19]]1932年,电影演员朱飞、王次龙、周文珠等人于10月28日到达香港与联合公司签约后,朱飞给《影戏杂志》写信称他住在香港青年会宿舍的七号房间,并称“每日无事,只能看看电影”;[[20]]“电影皇帝”金焰在港期间为帮助赈济难民的筹款,在1939年参加了由香港记者公会和青年会组织的篮球义赛,帮助该活动筹款共得一百一十九元八角。[[21]]除此以外,香港青年会自1904年起便多次免费放映电影用来招待香港青年,并且每次都伴随着牧师演说,进行宗教宣传。[[22]]在叶月渝看来,早期香港青年会的电影放映除了是新商品营销的工具,也是推进社会和宗教议程的工具,“电影把世界带到观众面前,并经常被用来说明基督教教义”。[[23]]虽然没有足够的关于在世纪早期由基督教会赞助的设施中观看了多少电影的信息,但20世纪早期有限证据表明香港青年会公开放映了纪录片,[[24]]在1908年到1913年间,香港青年会在介绍英国、加拿大、土耳其等国家的文化、风景、风俗历史的讲座中加入电影放映以提高讲座趣味性和公信力。[[25]]
在饶伯森的倡导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从1903年在宗教和智育演讲中开始应用幻灯片等新技术,在后续发展中又将教育电影加入进来。1907年清政府在提倡通俗教育的学务批示中也表示了对幻灯、电影等新式手段进行了倡导:
上海学界前会鸠资购电光活动写真一具,拟四出(处)试演,以期开通下流社会,现已定名通俗教育社,由社员赴内地开演,随演随讲”,并希望各地学务官员也照此“拟设通俗教育社先备电光活动写真一具,置备各种活动影片,忝揰试演,复延讲员随演随讲,相机指点。[[26]]
基督教青年会实际上延续了清末政府的这种通俗教育传统,自1910年起全国协会将电影作为社会教育和公共卫生方面的辅助教材。广州青年会1936年开始定期放映民众教育电影,无论是作为全国协会下属还是与广州青年会对照,香港青年会在其长久的电影放映活动中事实上已经肯定了“观赏电影是知性娱乐,是需要语言和智能所理解的娱乐”的观点。[[27]]
香港青年会在以“四育”为工作出发点的过程中“每事持一提倡之态度”,在智育方面提倡的智育演讲打破了香港各社团“仅以办学为限”的束缚,“常请各专家演讲各科学之新发明问题”,如饶伯森博士便受邀曾在香港青年会进行科学演讲与有声电影放映。[[28]]饶伯森一直致力于无线电学、热学等物理学方面的研究,1928年2月二次来华并开始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干事,而此次来华他还自备美国科学名家“福地脱”的最新发声电影,在1929年3月中旬到达广东进行了有声电影演讲和实验。[[29]]关于饶伯森在港进行有声电影放映的具体资料大多散佚,但从饶伯森于1928年11月便在上海青年会殉道堂进行试映有声影片及香港青年会对自身的历史梳理记载来看,[[30]]因发声电影“对于娱乐有莫大贡献,对于教育又相当裨益”[[31]],香港青年会理应也是在广州青年会放映前后邀请饶伯森进行的演讲与放映。
1925年到1927年香港的九龙大罢工导致了影院戏院的暂时关闭,香港青年会定期放映的国片和美国电影满足了当地观众的观影需求,其电影放映活动达到顶峰。[[32]]在基督教周报刊物《兴华报》详细记载过香港青年会对电影《不堪回首》的放映:
中国名画《不堪回首》一剧,前曾在港开影,凡已观者莫不叹为我国不可多得影片,剧情极为周密。闻此画已一连三晚在青年会大堂开影,并于礼拜三下午两点半学生半价,每晚得奇理仙度弦乐队名家到会奏乐助庆云。[[33]]
《不堪回首》是神州影片公司成立后制作的首部电影,由陈醉云编剧、裘芑香导演,1925年2月2日在上海大戏院试映时“因发券太多,楼上楼下乃无隙地”[[34]]。这一年前后,“《弃儿》《采茶女》《狭义少年》《苦儿弱女》《不堪回首》等皆次第输入港地,颇受欢迎,几有万人空巷先睹为快之盛况”[[35]],可见该片已在1925年与上海同步上映过。香港青年会的此次放映是1926年8月前后,由“已一连三晚开影”、“礼拜三日”学生半价、“每晚得奇理仙度弦乐队”等信息可以发现,青年会的本次放映是多次盈利性放映。
通过对创刊于1931年的香港青年会机关刊物《香港青年》的爬梳,对其几个重要的电影放映记载进行了整理,如表1所示,大致可分为商业放映和电影同乐会两类。从香港青年会对于这两种电影的描述来看总体来说是偏向于一种“高尚娱乐”的标准,不过在商业性放映中则更倾向于电影的质量,如在《杨太真》的放映预告中就说明了这部电影是“社会佳片”,“为杨耐梅主演,剧情光线均佳”[[36]];《宾虚》和《航空军》作为当时的舶来“巨片”,《香港青年》均在头版进行了特别预告,称《宾虚》“经过三年的摄制,耗费四百万金圆,配角十余万人,特别制造古代战船百余艘,描写罗马军人与海贼战争一场,血肉相博,战船相撞,其宏伟处,凡看过着无不惊异”,还称该片“全部天然彩色,美丽堂皇”[[37]];对于《航空军》的介绍则称其“背景极为宏丽而珍贵”,片中的“各设备战时移动,增人学识不少”。[[38]]此类商业放影活动从香港青年会在1930年的财务报告看,其在电影方面的款项支出为1520元,收入为2006元。[[39]]青年会在其财务报告中将关于电影的收入和支出均是放在事务科当中,可暂定其电影放映由事务科主导。
表1:香港青年会的电影放映
| 放映时间 | 放映地点 | 放映目的 | 放映片目 | 票价 |
| 1931年4月 | 中央会所大堂 | 商业放映 | 《杨太真》 | 会员一角,普通贰角 |
| 1931年12月 | 中央会所大堂 | 商业放映 | 《宾虚》 | 会员一角,普通贰角 |
| 1932年3月 | 本会 | 商业放映 | 《航空军》 | 会员一角,普通贰角 |
| 1931年10月 | 本会大堂 | 联络会员 | 凭证领券 | |
| 1932年10月 | 本会 | 电影同乐会 | 明星公司报效 | 凭证入场 |
| 1933年1月 | 本会 | 电影同乐会 | 皇后影院报效 | 凭证入场 |
| 1933年2月 | 本会 | 会友电影会 | 凭证入场 |
资料来源:《香港青年》杂志1931年到1933年各期。
相比商业性的电影放映,香港青年会在电影同乐会中只针对青年会会员的电影放映实际上应该是算作其群育或联络会员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在《香港青年》的四次电影同乐会的记载中均用了“特定于”某日进行放映的词汇,表明了这些放映活动均是在定期的放映之外对于内部人士的一种加映,其所放映片目也不一定与事务科具体的放映相同,甚至有事务科没有具体主导的可能性,1931年10月的放映是“少年部为联络会员感情起见”[[40]],1932年10月的放映是“少年部专为少年会友”,且1932年的这次放映还专门提及了电影是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热心报效”[[41]],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少年部主导的电影放映并非全部都能得到事务科的支持。同时,1933年1月的电影放映是“特为成人及少年会友举行春季电影同乐大会”,“由皇后影院报效”,从侧面还表明了香港青年会与当地的电影公司或者电影院、戏院等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关系。另外,香港青年会与香港电影界的联系与互动不仅有电影放映,还包括其他活动,如1935年香港青年会组织会员参观了一次电影摄制:
本会将于十一月十六日或二十三日星期六下午二时组织参观团,到七姊妹凤凰影片公司参观电影摄制,有志参加者请先到本会事务所报名……限额四十人,额满即止截,一俟该影片公司何日拍摄巨片通知本会。[[42]]
更为盛大的体现在香港青年会在举行35周年纪念庆祝中的“电影明星游艺大会”中:
本会以在此卅五周年纪念庆祝月中……特定于十一月八九两日下午七时半在本会大堂,开电影明星游艺大会,将入镜头之真态,移在舞台上表演,经得男女明星廿余位之赞助,届时莅场表演,义务效力。[[43]]
香港青年会组织会友参加电影摄制的新闻中表示这次活动是在事务所即事务科报名,可知在具体的运作中,事务科中应该是有人长期与电影界进行沟通,一则是为了能够租或买到电影得以在青年会中央会所大堂进行盈利性的放映,二则是进一步吸纳相关人员加入到基督教或者参与到青年会的社会服务中来,从而在电影界得到背书。香港青年会的三十五周年纪念中能得到二十多位在港男女明星在筹款表演方面的义务支持,并且表演《心病的爸爸》和《智谋》两部影片的经典场面,可见电影界对其支持之重。
无论是作为智育还是群育的青年会电影活动,都是青年会经由殖民政府和宗教社会组织推动的现代教育的拓展,特别是在中日关系局势日渐失控与中国危亡的时代背景中,即便是作为殖民地的香港也难逃对未来的窘迫感。不过,香港青年会仍然延续了20年代中期的商业性放映,一则为青年会的日常经营创收,二则是起到为精英阶层的高尚娱乐提供便利。由其带来的影响是香港的民众不仅要接受现代知识在道德上重要性,还在青年会包含着电影放映、戏剧表演、时局演讲等高尚娱乐活动中渐渐促成民族主义的兴起。香港青年会的电影放映,以及他们与知识界、电影界等文化精英的互动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兴起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44]]。
二、电影筹款与儿童剧场:战场外的救国公民培养
电影作为艺术或者文化消费品,除了娱乐功能外,更体现为教育功能。1935年香港教育界发起“电影清洁运动”后,何厌表示“教育而以电影为工具,却是教育方法的改良,提倡电影教育,对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都有莫大的助力”[[45]]。香港青年会在放映电影的过程中对此也是非常重视,结合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需要常进行配合的筹款放映,在《香港青年》的记载有两处:第一是在1931年广东地区发生严重水灾后,香港青年会不仅“发出捐款信封,向会友诸君募捐”,而且还专门举办了“影画筹赈会”,从8月10日开始一连六天每晚八时在中央会所大堂进行了电影放映,放映的片目包括程步高的《爸爸爱妈妈》、明星公司的《碎琴楼》以及欧美电影《虎穴幽兰》三部,“券价分两种,名誉券一元,普通券二角”;[[46]]第二是香港青年会在1920年左右设置了救伤队,“遇市内有火灾塌屋伤人之事发生,即之出处”[[47]],由于“年中所用药品费用浩繁,亟须筹措”,因此举行“影画及游艺筹款,入座券由全体队员担任动销”[[48]]。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与香港一水之隔的广东惠阳县大亚湾登陆并于21日占领广州[[49]],在广州的大部分大中学教会学校都搬迁至香港办学,在这些教会学校中都有学校青年会的存在,一般来说,无论是作为教育的电影放映还是作为筹款聚集人的工具,校内的电影放映均是由学校青年会以与城市青年会或影院合作的方式来主持,广州培英中学在迁到香港后继承了这种以电影积极参与社会公共议题与公共治理的传统,假座东方大戏院举行电影筹款以慰劳伤病难民,“将售券收入悉数汇赈白鹤洞、花地两区难胞”。[[50]]
救伤队和培英中学的电影筹款未提及具体的片目和其他信息,但三江水灾的影画筹赈会《香港青年》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爸爸爱妈妈》“在国产出品当中可算得最新颖,表演也最时髦,表现得非常沉痛”,《虎穴幽兰》“非常可观,属罕见的佳片”,《碎琴楼》是根据广东小说名家何诹的生平精心改编的,是“一部最哀绝的悲剧”。《爸爸爱妈妈》和《碎琴楼》偏向于伦理剧,而《虎穴幽兰》“以南洋虎豹大象出没之区为背景”,也是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美国的基督教会自从传入中国以后便在中国各地大办学校和医疗机构,通过一种相对软化的手段来传播宗教思想。结合新文化运动后的背景来看,“基督救国主义”在当时的社会里也不断被人提及,嵌构在中国近代社会救国与树人的两大主题中,特别是在1922年余日章提出中国基督教要实现“自治、自办、自筹”的方针后,更显得尤为重要。从效果上来看,救伤队和培英中学的筹款会暂未发现相关说明,但三江水灾的募捐结束后,香港青年会对该事件进行了报告,“映画收入银五百零四元二角正”[[51]],且在此次放映中香港青年会除了场地以外没有其他支出,“明达有限公司、胜利影片公司报效中西名画三部放映,聚珍印务书楼报效印刷画片本事三千张、传单一万五千张、入场券二千一百张。”[[52]]
在这里,以电影放映为核心的赈灾筹款或多或少看到香港青年会对当地社会的动员能力,在中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身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同外来的知识之影响形成的合流,将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诉诸其中,[[53]]反映出的也正是“人们对于自己地方社区的自豪感,作出对应的个人牺牲,为促进社会的福祉事业而从事慈善活动”的积极影响。[[54]]
电影放映在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时代里作为慈善活动的工具,实际上被赋予了聚集现代公民的作用与意义,因电影的“吸引力”而被迫纳入到公共领域当中,促成了社会民众的现代公民自我转化。同时,基督教青年会在放映过程中大多会选择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实际上已经不再只是对于基督思想的灌输,更多地是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联系在了一起。如岭南大学在1938年迁到香港大学借校舍办学以后,该校于1940年播放了医科教师嘉惠霖所拍摄的广州原校址影片,影片中的“建筑宏伟,风景优美”,自1938年交还美基会保管后曾开辟为难民区,“校内各物,并无损失,各种学术研究工作,亦仍旧进行”。[[55]]这里的原校址指向的正是故国的意象。在抗战前期,香港相对安稳,但其对国家的关注实际上也在构成对故国的观照态度,融入民族危亡的共同语境之中。
香港青年会在三江水灾的筹款中通过电影实现了香港居民对国家的建构并非是一个国际的香港,而是一个需要救亡的中国,以中国的影像故事的讲述与观看过程中完成了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构建与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民塑造。到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大批社会精英人士从内地到达香港躲避战乱,香港青年会积极与这些人合作在公共领域的民族主义构建与公民塑造就更为明显,特别是在救国公民的培养上也不再局限于成人。青年会少年部在1940年成立了儿童剧场,其目的在于构建“一种至少并不较低于学校的良好教育工具”,还聘请了曾昭森、许地山、傅世任、何中中、李圣华、蔡楚生、胡春冰、姚凤苏、黎民伟、刘伟民等知名的文化知识分子参与到指导委员会中。[[56]]在香港青年会少年部的主导下,儿童剧场理事会在1940年10月12日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儿童剧场”大会演出内容:戏剧、音乐、益智电影、公民训练、演讲、漫画等;
二、演出对象:义学学生、街童;
三、演出场所:青年会礼堂及各校礼堂;
四、理事会组织:函请未到各校于下星期六以前报到参加,各部组织决交第二次理事会讨论;
五、经费问题:商情青年会筹拨及函致中国文化协会补助外,并拟进行向本港各界人士募捐。[[57]]
从以上决议可以发现香港青年会的儿童剧场建设不仅包括戏剧表演,还增加了音乐、电影、漫画等娱乐内容,甚至还包括公民训练及演讲等与政治社会背景紧密配合的内容,其服务对象主要是义学儿童和街童等底层儿童。然而香港青年会的儿童剧场并不是国内首创,而是起源于苏俄,在美国也有一定的发展。不过国内早在1920年便对此有了关注,该年《教育杂志》翻译的国外文章不仅对儿童剧场中彼得格勒教育总长夫人的演讲进行了声情并茂地讲述,还重点从作者看过的一部话剧出发对儿童剧场的剧本创作进行了讲述。[[58]]到30年代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1937年前后国内关于苏联儿童剧场的介绍与日俱增,认为儿童剧团的产生是苏联“政府给予儿童充分公民权利”的结果,儿童剧场教育给儿童的“新社会主义生活的种种理论”不仅能帮助儿童摆脱来自社会的反动思想,还有利于儿童解放。[[59]]根据当时的相关政策,十二岁以下的儿童是不允许进入剧院的,儿童剧场的诞生填补了这种空白。
中国较早出现的儿童剧场在上海,由大晚报童友会和“我们的儿童剧社”共同主办,大约是从1936年12月中旬的开始了每周日的儿童剧表演。[[60]]当时影响力较大的儿童剧社是中国模范儿童剧社,该剧社几乎集结了当时中国文艺的知名儿童演员,如儿童电影演员陈娟娟、黎铿、葛佐治、胡蓉蓉、牟菱、李松筠、沈骏、王子淸,舞台儿童演员许璧、赵慧,儿童画家陈燃素、楼菊芳、周大贞、简而淸、简而和以及儿童小说家张银蟾等,顾问有潘公展、陈鹤琴、张善琨、应云卫、姚苏凤、宓季方等,平时专向各学校流动表演“教育性”戏剧。[[61]]淞沪会战之前,“特地集合了不能到前线去的小朋友们把演出所得的钱去购买大批的防毒面具和药物等类,托先锋剧社带去慰劳”,演出内容包括《梦游北平》《偷瓜》和《炮火中》等。[[62]]香港青年会成立儿童剧场时得到了蔡楚生、黎民伟、姚凤苏等电影人的指导与帮助,及能在短时间得到筹备正是复制了他们在上海时的中国模范儿童剧社的成功经验。
相比上海时期以文化界自主地儿童剧场建设只是单一的流动戏剧表演,香港青年会的儿童剧场不仅续接了战前全国性的儿童剧场运动,并且将场地固定在了青年会的礼堂和各学校的礼堂中,在内容上还进行了戏剧之外的娱乐方式,其在公开的倡导中明确了“儿童剧场活动中可以对儿童施以公民之训练”,“促进平民文化教育的水准,促进中国文化之进步”。[[63]]其实早在1924年青年会举行的第九次全国大会中,全国协会“深感公民为救国急务”,开始正是提出要推进公民教育运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期望通过公民运动对内让人民建立“广义的建设的纯正的爱国心,激发民治的精神,促进团体互助的觉悟,养成高尚的人格”;对外则要做好“缔结平等的互惠的新条约之准备”,还要通过“宣传泰西文化之优点,以备吾国改造之采择,发扬吾国文化之优点”。广州青年会是最早开始推动公民教育运动事业的城市青年会,后续北京、上海、太原、哈尔滨城市继续推进,主要形式包括公民演讲、公民研究团、公民宣讲队、国货展览、征文、演说、演剧或游艺会等,到后期还编制了相关教材,制作了幻灯片和活动影戏等。[[64]] 由此看来,香港青年会的儿童剧团用戏剧、电影、音乐等施以教育,对把儿童“养成为健全的国民,民族的勇士”[[65]]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儿童剧团的筹备期间,香港青年会还组织了一次“戏剧与儿童教育”为主题的座谈会,得到了中国教育学会香港分会、中国文化协进会香港分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香港分会的支持,并推选了许地山为主席,讨论了儿童剧团对于德育、智育、体育、群育和美育方面的价值。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香港青年会少年部联合在港文化团体组织的儿童剧场于1940年11月24日在娱乐戏院正式开演,除了香港青年会的林子丰、卢秉良等人对儿童剧团的筹备做了相关报告外,培英中学绿白剧团表演了《打错算盘》《小英雄》两部话剧,中华合唱团和圣保罗女中进行了《渡长江》《祖国之恋》等歌曲合唱,以电影放映谢幕。[[66]]截止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前,儿童剧团共进行过15次公开表演,大部分都包括了电影放映环节。[[67]]从其首次演出的效果上来看,儿童剧团“具有广大的意义,是教导我们,鼓励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到许多知识、经验、团结、合作等的好德行”[[68]]。
在儿童剧场的举办过程中究竟进行了哪些益智电影的放映由于史料的缺失暂时还未能补足,但可以从上海私立青年会中学校长田信耕在《兴华》杂志的相关文章一瞥青年会对电影之于儿童品格的态度。以教育的眼光看电影院,他认为电影院不仅是娱乐场所,也是教育机构,但其中放映的大部分电影对于儿童品格的形成来说是不合格的。通过对《电影造成的儿童》一书的介绍,指出电影在儿童对自身民族态度和认识上以及优秀行为习惯的养成有着巨大的宣传力,[[69]]结合青年会发起的公民教育运动,麦理安提倡发扬民族精神、揭示国耻事实、灌输国防知能、端正民众思想、表演象征刺激、促进新生活运动、提倡国民经济建设等七类教育电影的放映,大致可以推断出儿童剧场应该会就此类片目进行放映,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观看教育电影的人在“吸引”下“不断地受到重大的影响”。[[70]]
三、随军服务团电影队在前线的娱乐教育事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华工加入到欧洲前线中,1917年底在法中国人总数有五万四千人,到了1918年底就增至九万六千人,华工的营地不仅会遭到德军飞机或者炮弹的袭击,而且还会因为水土不服而染上恶疾,除此以外他们还遭受着欧洲当地人的眼中歧视。面对这种情况,基督教青年会在一战中的军人服务队开始向当地华工提供了大量的服务,特别将经历集中在了休闲活动和中国人的公共教育问题上。[[71]]在公共教育方面,基督教青年会帮助华工在短时间内提高了识字率,源源不断的家书自这时起开始寄往中国。在休闲活动方面,为了降低“不那么有益的娱乐方式”对士兵的吸引,美国的威尔逊政府开放了营地,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战争工作委员会在营地中建造并配备了许多社会和娱乐建筑,也被称为“小屋”,其中较大的包括礼堂在某些情况下可容纳2800名士兵,主要提供业余用品,还免费提供小区剧院、音乐表演、信息讲座和电影。[[72]]英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在欧洲战场上开辟了77家战时电影院,其中大多数是便携式装置,可向士兵免费提供电影,在主要的军队大本营中,还有20个专门建造的电影院,每个剧院可容纳1500名士兵。[[73]]长期儒家伦理的教育与习俗的约束,华工并不像欧美各国的士兵一样要电影来缓解“急需的有害娱乐手段”,但包括电影在内的娱乐活动确实为他们提供了分散“当前冲突恐怖”注意力的作用。[[74]]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正是看到了“一战”中基督教青年会所取得的作用与效力,在1932年的“长城之役”和1936年中的绥远战争中便以全国青年会的名义开始了军人服务工作,为前线上的士兵进行慰劳、娱乐、教育及救护等事工。“卢沟桥事变”后,保定青年会率先发动军人服务工作,在全国协会的推动下,“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委员会”短时间内便得到了成立。[[75]]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军人服务主要有驻营服务、随军服务和战地服务三种方式[[76]],内容“多注意教育娱乐和精神慰劳,伤兵的工作要占百分之七十”[[77]]。就在全国抗战状况极度严重之时,“全国一致为民族生存而与敌人同归于尽”,“中国全民全面应战,广东的责任和贡献逐日增加”[[78]]。广东的军人也被抽调北上,广州青年会为“集合爱国志士对前线浴血抗战之将士做直接之效劳,使能鼓舞精神,增加力量”,遂在其战时工作委员会的主持下成立了由干事李圣华带队的十人随军服务团于1937年11月随邓龙光的军队在南京、武汉、长沙、仁安等地活动。[[79]]与早期全国协会的军人服务部所进行的驻扎式服务不同,广州青年会随军服务团是“跟随着军队进退而未有固定工作地点的”[[80]]。
到了1938年应薛伯陵邀请,随军服务团期冀回到广州进行第二期人员征集的时广州已经开始不太平。广州青年会遂派随军服务团团长邓锦辉及救护队队长吴文伟与香港青年会进行了接洽,起初是为了进行物资征集和救护车、卫生材料的征求,[[81]]但香港青年会在民族危亡时刻也积极响应,并与广州青年会合作组建起了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在很快时间内征集到了二十四人,于8月20日下午在青年会举行发拨旗礼[[82]],并“环游中环一代,全体服装整齐,精神健旺,侨众于彼等经过时,均予以同情与敬佩之注视”[[83]],在广州进行一周左右的培训后,他们便北上南浔线,服务于商震、吴奇伟、叶肇等部。之后,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分别于1939年1月、1940年1月和1941年6月进行了三次续派,先后有一百三十七人周游于苏鄂湘赣粤桂等六省,“为五十万前线忠勇将士及百余万战地乡民而服务”。[[84]]
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的服务方式虽是非固定的,但其在对军人的服务内容与全国协会大致相同,主要集中在军官俱乐部、军人俱乐部、伤兵招待处、医院服务处等建设工作,他们不仅在前线设立站所救护伤病难民,还在后方设立中山室(即俱乐部)以娱乐教育军人,从1937年第一次进入内地开始便携带了电影机、留声机、幻灯机及书报等文化娱乐教育设备并进行随军娱乐教育事工。[[85]]从其首次出发时的赞助宣传中可以发现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的电影设备是出发前购买的,其中电影机、发电机和附件共花费了一千一百六十元。[[86]]不过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随军服务团回汉口途径武进、丹阳时遇到了敌机多次追击,“带来的娱乐用具如电影机、留声机、幻灯机、收音机等因不及携带,均放置在某地友人家中,一时无从领回应用”[[87]]。至于后来这些设备如何回到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暂时还未出现相关史料,但其电影放映确实是贯穿了整个全面抗战爆发到香港沦陷之前的大部分时间段。
在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的俱乐部中,不仅举行各种球类比赛及军民联欢大会促进军民合作之精神,他们的电影放映对象也不仅限于伤兵和军官,还包括出征军人的家属。除此以外,电影队还“协助东江一代春礼劳军运动筹款约万元,协助省民教馆筹建民众礼堂得款约五百元,又协助广东各界前线慰劳团放映电影于从化、佛岗、英德、新丰等地,协助粤港基督教慰劳团放映电影于增从英佛两线上”,还为后方民众团体提供了四套电影片。其中,为省民教馆筹款时所放映的影片为中国制片厂出品的抗战名片《保家乡》和《热血忠魂》。[[88]]同年粤港服务团在到达广西后,“该团电影队十二日承省府之约,在省府礼堂放映中央电影场出品抗战名片《保家乡》,剧情内容表现军民合作与抗日情绪,甚为扬溢。十三日晚七时在公共体育场公开放映,招待本市民众”。[[89]]同时,为了充分发挥电影在前线的宣传娱乐教育作用,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在各地设立社会服务处进行电影放映、歌咏、戏剧演出等流动宣传工作共计百余次,观众四十余万人。[[90]]从1939年的《中国基督教年鉴》来看,毋论是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的电影放映,单单是1939年的7- 9月三个月的时间内,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服务总结中电影和戏剧的出席便达到了274334人次。[[91]]1941年南宁收复后,《大公报》香港版在对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团长邓锦辉的采访中介绍他“统帅救护队电影宣传队在增从线之青塘、粤汉铁路正面之佛岗、广西之柳州一带活动”[[92]],一个团长负责救护与电影也从侧面说明了电影放映在粤港服务团中已经成为仅此于伤兵救护之外的重要事工。
尽管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有着未沦陷的香港作为大后方,但其主要经费物资还是主要来自国内外的爱国热心人士募捐以及中央政府的拨款。[[93]]除了首次出发前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进行的物资征集中涵盖了电影机等相关设备与工具外,他们在1940年和1941年的物资募捐中也包括了电影放映或拍摄的相关设备。1940年第四期服务团出发前,粤港青年会的征集清单中便包括了“十六咪哩放映机一具、电影画片二千尺、活动菲林一千尺”[[94]],而在1941年的第五期出发时团长邓锦辉所做的报告中明确物资征集“重质不重量,以必需品为最合适,此外团部所需工具,如活动影片(十六米厘)、留声机及唱片等”[[95]]。
从他们征求16毫米电影的设备和胶片可见粤港服务团的在前线放映的电影多来自香港各界的捐助,前文中提到香港青年会长期保持着与电影界合作亲密的关系也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其次从青年会全国协会军人服务团的经费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资助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论,当时坐落在重庆属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直接领导的中央电影场制作了如《保家乡》《长空万里》《中华儿女》《孤城喋血》等优秀的影片[[96]],作为战时用以鼓舞士气的重要工具,无论是“不应以营业为目的”的中央制片场的直接提供,还是香港电影界的捐助在民族救亡的背景中都显得尤有极大可能。因此,包括粤港服务团在内的军人服务团体所进行的电影放映也处于流动状态,并没有像“一战”期间基督教青年会在欧洲战场中一样建立起军营里的电影院,但他们“一切一切的工作无不使军兵兴高采烈,增加抗战的情绪,不致因身体的痛苦而影响精神颓靡”[[97]]。除了激发抗日情绪的故事片、纪录片或新闻片的放映,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工作要项中鼓励“选择适合军人生活或战地常识之影片的巡回放映,印发说明,分别放映于支部驻扎地点,俾便介绍其近代知识”[[98]]。
随着抗战进入持久战阶段,因为物资的短缺或者通讯中断,国共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国军”以青年会的军人服务有“通共”之嫌而予以过取缔,到1942年大部分青年会的军人服务团体实际已经自行解散,赵晓阳仍然评价青年会的随军服务是“抗战以来历时最长、范围最广的活动,它没有波澜壮阔的气势,没有歼敌千万的喜讯,但细声润物,温暖着每个战区、每个官兵”[[99]]。尽管如此,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依然活动在粤桂区域,其长期进行着的电影放映活动事实上不仅激发了军民共赴国难的爱国热情,也活跃了军营或前线沉闷的气氛,间断为驻地民众的放映也为他们带来了精神的慰藉。[[100]]
结语
借助于相对发达的城市经济和文化消费环境,电影放映在战前香港长期处于商业竞争较强的状态,自晚清以来的通俗教育、平民教育、电影教育等运动因殖民地政府长期对学校教育等事业的把持也造成了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小,以至于在抗日战争发生之前香港青年会的电影放映均较为零散。直到“九一八事变”以后内地影人及文化界人士陆续“逃港”,香港青年会对电影放映之于社会服务、人格培养等方面的作用才不断得到加深,不仅在后方进行“影画筹款”以支持内地的自然灾害和抗战事业,通过集结在港的文化电影界人士组成儿童剧团进行戏剧电影活动以达到对儿童的娱乐教育,促成从儿童到成人多年龄段的救国公民的培养与塑造;他们在战场前线与广州青年会联合组织的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寓教于乐,在推动军人进行“健康娱乐”的同时还促进了军民大团结,提升了整体抗日情绪。在此经验基础上,香港青年会于战后保持了设立电影队进行流动放映教育电影的事业,“除每星期在中央会所及九龙支会放映招待会友”外,还积极参与“各学校工厂的邀请放映”[[101]],包括教育卫生等片,1949年还专门购置了影音工具及宗教、体育、智育等片以应各界需求。[[102]]
一部中国的近代史,便是中国民族救亡和新人培养的现代社会转型历史,尽管香港自1842年以来便背负起殖民地身份的枷锁,但香港居民对中国前途的关注从未停止,特别是进入抗战期间,作为香港社会团体一份子的香港青年会面对家国危难以包括电影在内的娱乐教育不仅“对塑造青年人的健全人格,引导青少年健康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03]],更是在以青年会为公共领域进行的多维度议题参与,在公众舆论的设置中形成以民族主义为主导的强制力量,在精英阶层和平民百姓的对话与沟通建构起救国的现代公民品格,“从公众拓展外推至从文化批判公众股向文化消费公众的拓展与之并行的转型”[[104]]。
Film Screenings of the Hong Kong YMC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1-1941)
ZHANG Shilin (Beijing Film Academy)
Abstract: Since 1904, the Hong Kong YMCA has been screening films in its central clubhouse, both commercially for the YMCA's own operations an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elite for "wholesome and useful entertainment" and civic education for YMCA members.After China entered the parti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Hong Kong YMCA continued the above two types of film projection while using film to raise funds for the national salvation cause and to serve the community, promoting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cultivating sound modern citizens through the drama and film activities of children's theater group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Hong Kong YMCA and the Guangzhou YMCA jointly formed the Guangdong-Hong Kong YMCA Military Service Corps and set up a film crew to go north with the Cantonese army and conduct mobile film screenings, bringing spiritual comfort to the soldiers and inspiring patriotic enthusiasm among th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to go to the country together.
Key Words: Film-Screenings, the Hong Kong YMCA, Hong Kong Film Culture, Anti-Japanese War
[[1]]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的狭义概念主要指基督教男青年会。在中国近代史中,基督教青年会运动虽然也对基督教男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等进行了区分,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基督教男青年会运动的范围及深度都要远远大于女青年会和和学校青年会,更多时候体现为男青年会的下属或旁支,因此本文采用包含着三种青年会的广义概念。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基督教男青年会位于必列啫士街,女青年会位于般含道,九龙支会位于窝打老道东方街口。
[[2]]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史略》,《香港青年》1935年第3卷第21期,第162-164页。
[[3]] 逸庐主人编,《香港九龙便览》,中华书局1940年,第74页。
[[4]] Ruth L. Packard, “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1935—1936 (China)”. Ph.D. di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1, p.1.
[[5]]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长沙办事处:《全国协会长沙办事处通函》,《协会消息》1938年第1卷第1期,第7页,
[[6]] 震元:《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四十周年纪念》,《香港商报》1941年第172期,第12-14页。
[[7]] 张隽隽:《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电影放映活动初探(1907-1937)》,《当代电影》2016年第6期,第86-93页。
[[8]] 菅原庆乃:《走向“猥杂”的彼岸:“健康娱乐”之电影的诞生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年第29期,第151–175页。
[[9]] 《全国协会民国二十四年事工报告》,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民国二十四年》,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5年版,第1-17页。
[[10]] 易翰如:《香港之电影事业》,《电影周报》1925年第2期,第9页。
[[11]] 朱寿桐主编:《中国新文化百年通史》(上卷),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8页。
[[12]] 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晚清七十年折射中国转型困境》,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第208页。
[[13]] 美国在华的活动延主要是基督教会事业,20年代30年代还是集中于教育医疗和培训,以及面向社会、基础更为广泛的项目,在1920年,在中国居住的六千六百三十六位清教传教士多半是美国人,他们组成许多小的传教站分散到全国各地。参见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1600-1949)》,温洽溢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99页。
[[14]]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1600-1949)》,温洽溢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78、463页。
[[15]] 清华学校编:《游美同学录》(上),《近代史数据》(第123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7、190页。
[[16]] 陈刚:《上海南京路电影文化消费(1896-1937)》,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
[[17]] 黎民伟有严珊珊和林楚楚两位夫人,严珊珊于1914年1月与黎民伟成婚后怕自己参与社会活动不能满足黎民伟对家庭和爱情的期望,就在1919年遇到林楚楚后主动撮合了两人。本次新年欢叙会发生于1917年,可以推定这里的黎民伟夫人为严珊珊。参见张密珍、万珺之,《黎氏家族:奇特婚姻,三代影人》,《电影》2011年第10期,第66-72页。
[[18]] 《新年欢叙大会》,《青年进步》1917年第1期,第4页。
[[19]] 林曼叔:《鲁迅赴香港演讲经过的几点质疑》,《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9期,第22-31页。
[[20]] 开末拉,《朱飞二十八日抵香港 无处游玩 专看电影 寓中华青年会宿舍七号房间》,《影戏生活》1932年11月3日,第1版。
[[21]] 《篮球义赛收入成绩美满》,《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10月23日,第7版。
[[22]] 周承人、李以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虽在其论述中提及到香港青年会在1904年便开始电影放映活动,但二人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始史料,因此香港青年会具体的起始放映时间虽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但本文先采纳了周、李二人的结论。周承人、李以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第17-18页。
[[23]] Emilie Yueh-yu Yeh, “Translating Yingxi: Chinese film genealogy and early cinema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2015, 9 (1): 76-109.
[[24]] Chiu-han Linda LAI, Producing heterotopia: Traces of the cinema in the thick space of governmentality, loc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1934, Hong Kong. New York University, 2006, p. 146
[[25]]Emilie Yueh-yu Yeh, “Translating Yingxi: Chinese film genealogy and early cinema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2015, 9 (1): 76-109.
[[26]] 《新闻录要:学务-提倡通俗敎育批示》,《北洋官报》1907年第1355期,第11页。
[[27]] 菅原庆乃:《走向“猥杂”的彼岸:“健康娱乐”之电影的诞生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年第29期,第151–175页。
[[28]]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史略》,《香港青年》1935年第3卷第21期,第162-164页。
[[29]] 《放影破天荒的发音电影预告》,《广州青年》1929年第16卷第6期,第24页。
[[30]]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外籍工作人员饶伯森博士在该会殉道堂试映影片》,上海华年http://memory.library.sh.cn/node/68079。
[[31]] 《本会放影有声电影预告》,《广州青年》1933年第20卷第26期,第175页。
[[32]] 参见《青年会影画》,《中国邮报》1925年2月2日;《演映中国名画<海誓>》,《中国邮报》1925年12月1日;《影幕消息》,《中国邮报》1926年1月19日;《影画消息》,《中国邮报》1927年5月16日。
[[33]] 《青年会开映国画(香港)》,《兴华》1926年第23卷第32期,第31页。
[[34]] 《评<不堪回首>》,《时报》1925年2月3日,第10版。
[[35]] 易翰如:《香港之电影事业》,《电影周报》1925年第2期,第9页。
[[36]] 《电影消息》,《香港青年》1931年第4期,第27页。
[[37]] 《放影世界名画<宾虚>》,《香港青年》1931年第12期,第1页。
[[38]] 《放影航空冒险名画》,《香港青年》1932年第3期,第1页。
[[39]] 《民十九年1930财政报告》,《香港青年》1931年第2期,第11-13页。
[[40]] 《少年会友电影联欢会》,《香港青年》1931年第10期,第3页。
[[41]] 《会友电影同乐大会》,《香港青年》1932年第9期,第4页。
[[42]] 《参观电影摄制》,《香港青年》1935年第3卷第22期,第3页。
[[43]] 《电影明星游艺大会》,《香港青年》1935年第3卷第22期,第4页。
[[44]]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2页。
[[45]] 何厌:《电影教育问题》,《红豆月刊》1935年第3卷第6期,第177-179页。
[[46]] 《影画筹赈三江水灾》,《香港青年》1931年第13期,第1页
[[47]]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史略》,《香港青年》1935年第3卷第21期,第162-164页。
[[48]] 《本会救伤队影画游艺筹款》,《香港青年》1933年第1卷第8期,第4页。
[[49]] 莫世祥、陈红:《日落香江:香港对日作战纪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页。
[[50]] 《本港简讯·广州培英中学慰劳伤病难民筹款》,《大公报》(香港版)1938年12月27日,第6版。
[[51]] 《结束募捐赈款之报告》,《香港青年》1931年第15期,第4页。
[[52]] 《鸣谢二则》,《香港青年》1931年第15期,第4页。
[[53]] 陈兼、陈之宏:《译者导言》,(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37页。
[[54]] (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70页。
[[55]] 《放影广州原校址影片》,《岭南大学校报》1940年第84期,第4页。
[[56]] 《港青年会成立儿童剧场》,《中国商报》1940年11月4日,第5版。
[[57]] 《儿童剧场昨日首开理事会》,《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10月13日,第6版。
[[58]] 《欧美教育新潮:俄国的儿童剧场》,《教育杂志》1920年第12卷 第11期,第8-9页。
[[59]] 《苏俄的儿童剧场》,《戏剧艺术》1937年第1卷第4-5期,第11-15页。
[[60]] 林蜚,《一九三六年的冬季 剧坛活跃情况的展望》,《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11月28日,第16版。
[[61]] 《儿童剧社 将演国防剧 全体小明星均参加》,《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8月10日,第7版。
[[62]] 端木禄增:《访问中国模范儿童剧社:几十颗儿童的心在活跃的跳动,他们齐说救国也是我们的责任》,《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8月11日,第10版。
[[63]] 《儿童剧场昨发告青年书 呼吁社会人事予以赞助 定十九日举行理事叙会》,《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10月16日,第6版。
[[64]] 余日章:《公民教育运动说明书》,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1926年。
[[65]] 居尹:《儿童剧场》,《扫荡报》(桂林版)1939年6月27日,第4版。
[[66]] 《儿童剧场明日开幕》,《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11月23日,第6版。
[[67]] 《儿童剧场第十五次公演 廿六廿七两晚》,《大公报》(香港版)1941年9月26日,第6版。
[[68]] 《儿童剧场昨开幕 赴会者千余人盛极一时》,《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11月25日,第6版。
[[69]] 田信耕:《电影与儿童品格》,《华年》1933年第2卷第37期,第9-11页。
[[70]] 吴明:《公民训练的教育电影教材》,《教育辅导》1936年第2卷第5期,第23-25页。
[[71]]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1600-1949)》,温洽溢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88-389页。
[[72]] Collins S. Film, “cultural policy, and world war I training camps: Send your soldier to the show with smileage”. Film History. 2014;26(1):1-49.
[[73]] Hanna E. “Putting the Moral into Morale: YMCA Cinemas on the Western Front, 1914-1918.” 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2015;35(4):615-630.
[[74]] Peter Chen-Main WANG, “Caring Beyond National Borders: The YMCA and Chinese Laborers in World War I Europe”. Church History. 2009, vol. 78, no. 2, s. 327-349.
[[75]] 《三年来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工作概况》,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三年来的军人服务(中英文对照)》,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1941年,第1页。
[[76]] 赵甘霖:《香港青年会非常时期工作一览》,《同工》1939年第182期,第35-39页。
[[77]] 江文汉:《全国区青年汇的军人服务工作》,《协会消息》1938年第1卷第1期,第3-7页。
[[78]] 李应林:《本会随军服务团的组织》,《广州青年》1937年第25卷第17期,第1页。
[[79]]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组织随军服务团到前线去》,《广州青年》1937年第25卷第17期,第2-5页。
[[80]] 李圣华:《广州青年会随军服务团近讯》,《协会消息》1938年第1卷第1期,第15-16页。
[[81]] 《简讯》,《申报》(香港版)1938年8月08日,第4版。
[[82]] 《简讯》,《申报》(香港版)1938年8月20日,第4版。
[[83]] 《简讯》,《申报》(香港版)1938年8月22日,第4版。
[[84]] 《粤港青年会遣派随军服务团回国》,《华侨先锋》1941年第2卷第24期,第22页。
[[85]]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半年来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工作概述》,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1938年,第13页。
[[86]]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组织随军服务团到前线去》,《广州青年》1937年第25卷第17期,第2-5页。
[[87]] 李圣华:《广州青年会随军服务团近讯》,《协会消息》1938年第1卷第1期,第15-16页。
[[88]] 《粤港青年会服务团抵韶》,《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4月12日,第5版。
[[89]] 《港粤服务团在桂向李主任献旗》,《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10月18日,第5版。
[[90]] 《粤港青年会遣派随军服务团回国》,《华侨先锋》1941年第2卷第24期,第22页。
[[91]] George A. Fitch, “The YMCA Emergency Service to Soldiers”.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40, pp. 318-323.
[[92]] 致华:《南宁收复经过——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团长谈话》,《大公报》(香港版)1941年1月8日,第6版。
[[93]] 赵晓阳:《抗战时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本土化探索——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第700-719页。
[[94]] 《粤港青年会组织随军服务团出发前方》,《同工》1940年第186期,第50-51页。
[[95]] 《青年会服务团定期出发桂粤服务》,《大公报》(香港版)1941年5月28日,第6版。
[[96]]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第59-65页。
[[97]] 赵震寰:《我们对于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之感想》,《协会消息》1938年第1卷第1期。
[[98]] 《三年来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工作概况》,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三年来的军人服务(中英文对照)》,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1941年,第8页。
[[99]] 赵晓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第31-39页。
[[100]] 卢海标:《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在韶关的爱国救难活动述评》,《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39-42页。
[[101]] 《香港青年会电影队巡回放映》,《同工》1948年第2卷第8期,第62页。
[[102]] 《香港青年会电影队消息》,《同工》1949年第3卷第2期,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