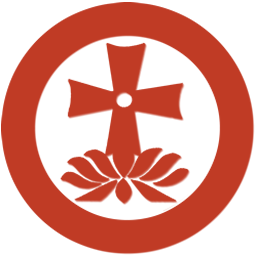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1年第16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155
刘如梦(上海大学)
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拉开了中西交流新的序幕。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们为打开在中国的传教之门,一方面采取“文化适应性”的策略,另一方面,采用学术传教的手段,双管齐下,以期赢得中国士大夫及统治者的支持,希望自上而下,最终达到皈依中华的目的。其中,学术传教的手段即以“科学充当诱饵的作用”[1],通过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知识,赢得士人乃至统治者的青睐与信任。在传教士传播的西方科学知识中,为中国统治者所重视的天文学知识最为丰富。
对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中的政治、权力等因素的研究,学界已多有论述,如张柏春《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指出朝廷的政权状况、皇帝的态度和开明与否对于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马伟华《历史宗教与皇权》认为,适应明清时期的皇权政治是保障耶稣会士在华顺利传教的根本,同时,皇权的态度决定了历法改革和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命运。[3]江晓原《欧洲天文学在清代社会中的影响》指出,导致中国天文学未能继续前进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皇家天文学的“政治巫术”性质。[4]
上述研究虽然对明清天文学在华传播背后的政治、权力因素作了一定的探讨,但并不够全面细致。本书作者长于中西文献互证,广泛收集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资料,其中有些资料是前人所未注意到的文献,如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所藏汤若望《天文实用》、巴黎天文台所藏《御制历象考成表》、巴黎天文台藏洪若天文观测手稿等,通过对发现的中西文献的相互补正,就观星台事件、1711夏至日影观测事件、蒙养斋算学馆成立等个案事件抉微发覆,较系统地呈现出了顺治至道光年间欧洲天文学在华传播的历程,其中,康熙一朝尤为本书的研究中心,作者的研究显示出康熙帝运用其至高无上的皇权,既保障了西方天文学在华的传播,又阻断了西方天文学在华的进一步传播。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入华之际,正逢中央王朝改历、修历需求颇为凸显之时,然而,参照西历进行改历、修历无论是在明末还是在清初,都充满着争议、斗争。[5]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中国古代王朝,“改正朔,易服色”等活动,本就被认为事关王朝的统治合法性,修订立法,不仅仅是一项学术性的活动,还是一项政治性的活动;另一方面,携教入华的传教士深为保守士人所忌惮,在保守士人看来,天主教并非中土圣人之教,西洋人入华动机在“谋人之国”,因此“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祥;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之无日也”。以杨光先为代表的保守人士对西洋人的仇视可见一斑。[6]西方天文学在华的传播,注定杂糅着政治、权力、宗教等多重因素。
在推行西方历法备受争议的情况下,康熙帝保障西法在华的推行,又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作者认为,历法之争是康熙学习西方科学的直接原因。事实上,康熙初年,西洋历法优于传统历法,已是十分明显的事实,采用西洋历法,对于初创帝国的稳定与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书中详细介绍了康熙年间三次日影观测事件,分别为1668年午门日影观测事件、1692年乾清宫日影观测事件和1711年夏至日影观测事件。其中,南怀仁所代表的西洋历法在1668年午门日影观测中获胜,验证了西法较之传统历法的准确有效,最终促成了历法之争的翻案,奠定了西洋历法的主导地位,此次日影观测事件也激发了康熙帝对于西学的兴趣。此外,作者指出,康熙帝“重视科学,不仅仅出于兴趣和治理国家的需要,有时还出于权术的考量”。书中详细考察了1692年乾清宫日影观测事件和1689年观星台事件的始末,揭示了康熙皇帝煞费苦心地运用西方科学新知以达到慑服、控制汉族大臣的企图。这两起由康熙帝精心导演的事件,塑造了康熙帝精通历算知识“圣明天子”的形象,“直到1702年,康熙帝还说‘汉人于算法一字不知’”。[7]西洋天文新知被康熙帝利用为巩固自身权力的工具。
那么,康熙帝是如何保障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的呢?本书展现了康熙帝保障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所做出的多种努力,包括重用、延揽南怀仁等耶稣会士;成立蒙养斋算学馆;培养本国算学人才;开展历法改革以及进行大地测量等等。可以说,为保障西方科学知识在华的传播,康熙帝提供了包括政策、财力、人力等多方面的支持,其对吸收西方科学所展现出的兴趣和所做出的努力,毋庸置疑是明末至清末的历代帝王所不及的。
在康熙帝的保障之下,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的情况又如何呢?在作者看来,康熙朝是中西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中西交流一个新的时代,这一时期,“新知识大量传入,不仅有哥白尼、开普勒学说,还有卡西尼、腊羲尔的新观测结果,大量科学仪器也随之传入,玻璃、珐琅等技艺也在宫廷得到仿制”。[8] 然而,中国实现科学近代化的目标,并没有在康熙时代来临,甚至康熙时代之后,中西交流一度陷入近乎停滞的状态。在作者看来,“科学的近代化关乎传播和接受两个方面”,“接受方对西学的态度如何也影响了科学的传播。首先,作为皇帝,康熙的态度最为重要”。[9]
那么,康熙帝在保障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的同时,又为何会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西方天文学在华的传播呢?从本书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数点原因,其一:康熙帝吸收西方天文学,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提高自己作为满族君主的文化权威,从而更好地控制汉族臣子、士人,他并不想将西方新知及时传入社会大众;其次,“西学中源”说在康熙帝的宣扬下,成为庙堂之说,影响了梅文鼎、梅文鼎之孙梅瑴成、何国宗等宫廷文人,这些宫廷文人又转而影响了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等,完成了对西学态度从朝廷到江南的转变,“西学中源”说助长了国人盲目自大的情绪,妨碍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独立地、深度地传播;最后,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深受康熙帝个人兴趣的影响,然而,这种个人的兴趣最终并没有使得中国科学的发展走向制度化。一方面,康熙帝以个人理解、好恶对西学新知妄加褒贬,限制了西学的传入,另一方面,康熙帝也无意于彻底仿效西欧,如法国皇家科学院,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制度。雍正往后,清朝帝王对于西学的兴趣日益淡薄,西方科学在华不再受到重视,中国与欧洲科学的差距也随之不断拉大。
从本书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康熙帝面对西方天文学时复杂、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康熙帝欲利用西方天文学作为操控、慑服汉族臣子的手段,另一方面,他又动用皇权为“西学中源”说张目,著《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一文,声称西历传自中国。康熙帝为何呈现出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作者认为,康熙帝此举在于平息由中西学说不同而产生的争论,为学习西学寻找借口。[10]或许这种心理还源于康熙帝对自身“道治合一”即“君师合一”圣王形象的塑造。为塑造这种形象,“除了推崇理学、尊孔祭孔等一系列对儒家文化信仰的昭示,还需在文化、理论层面胜过“道统”一贯的执掌者——士大夫阶层”,“除了对儒家文化勤学不辍,学习与掌握西方科学也在康熙帝塑造‘知识权威’形象的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1]如果我们以这种视角去审视,那么康熙帝在日影观测事件、观星台事件中的种种“好为人师”的表现,似乎便可以理解了。康熙帝在中国传统历算知识之外学习西方天文知识,又反而将西方天文知识纳入中国传统历算知识的范畴,其目的便在于证明自身虽出于异族,但君临华夏却具备了超过士大夫阶层所拥有的道统知识储备,足够有“为君为师”的资格。《清史稿》称康熙帝“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12]可见康熙帝对自身形象塑造的卓有所成。
本书引发我们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康熙帝的皇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障和阻断西方天文学在华的传播?康熙帝是否曾经真的有机会在他的“乾纲独断”之下实现中国的科学近代化?康熙帝时期西方科学在华传播热闹一时,但随着康熙帝的逝世,迅速偃旗息鼓,颇有人走茶凉之感。分析明清时期的社会环境,似乎还不具备接纳西方天文学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的大量传入的条件,西方天文学知识的传入“……受到了来自当时文化、政治、学术氛围、学者们的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新的天文学知识观念,“……势必会引起传统知识体系的混乱”。[13]而当时的中国社会,也不具备吸收、应用西方科学,继而实现科学知识再生产的社会条件,西方天文学传入后,只是在宫廷科学家、知识分子和民间文人中得到认识,距离在民间社会的广泛应用,创造财富价值还为时尚早。康熙帝自身的兴趣勃发、勤学不辍,可能为西方科学的在华传播掀起了一时的波澜,但真正改变中国科学发展的轨迹,似乎凭借其至高无上的皇权也是无法办得到的。
作者在书中对以上两个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但这并不妨碍本书的学术价值。本书除在宏观上展示了顺治至道光年间,尤其是康熙时代天文学在华传播的整体情况外,还通过中西史料互证,梳理史实,对发生在康熙年间的一些重要历史史实作了考证。作者揭示了观星台事件与理学名臣李光地培养西学兴趣之间的关系,观星台事件中,汉族重臣李光地为讨好康熙帝却适得其反,遭到康熙帝的斥责,为迎合康熙帝对天文历算的兴趣,李光地遂而向梅文鼎学习天文历算知识,并最终再次赢得了康熙帝的赏识。作者对照西文文献,指出中文文献《历象本要》中所记载的“壬午(1702)冬,銮舆南巡,命皇子领西洋筹人,自京城南至德州七百余里,立表施仪,密加测望”中的西洋筹人,即指耶稣会士安多,揭示了安多在子午线测量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作者还通过对安多《数学纲要》、黄百家《学箕三稿》的考察,指出黄百家所记录的哥白尼学说应系安多所介绍。作者通过研究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的“誓状”、“公书”等史料,详细再现了“礼仪之争”中耶稣会士向钦天监奉教天文学家取证的史实,探究了“礼仪之争”中奉教天文学家对祭祖、祭孔的看法,并且,通过研究被译成拉丁文的“誓状”,作者指出了黄一农《被忽略的声音》一书中的一处错误,黄一农在该书中认为焦保禄是焦应旭,作者指出焦保禄为焦秉贞,而非焦应旭。
作者长于宫廷史的叙述,通过中西史料的互证,将隐藏在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背后的宫廷政治、权力斗争历史娓娓道来,并对这段历史中传教士、君臣、士人等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作了详尽的考察,从文化传播者与接受者两个角度,客观呈现了这段中西交流史。本书截取叙述的时间段虽在明末到道光年间,嘉庆、咸丰年间欧洲科学新知在沿海城市的传播以及被不断更新的复杂过程也在附录二《新教传教士与天文学的传播》中略有叙述,但其叙述重点仍为康熙一朝,康熙一朝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情况占据了本书绝大部分篇幅。因此,本书有助于读者系统客观地认识康熙年间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情况,也有助于读者进一步认识康熙帝在这段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指出以往有学者认为耶稣会士所传播的科学是过时的、落后的观点是显然过于简单化的,应当说作者这种评价是客观公允的。张柏春就曾指出,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要比中国人实际接受得多。[14]江晓原则指出,明清时代欧洲天文学在华传播一度使中国接近了欧洲天文学发展的前沿,哥白尼学说等最新的欧洲天文学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及时引进了。[15]在康熙帝皇权的保障之下,当时欧洲天文学知识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那么中国又为什么没有在康熙时代走向科学的近代化?这其中,康熙帝皇权所扮演的保障与阻断双重角色令人深思。
[1] 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耿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7页。
[2] 张柏春:《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0页。
[3] 马伟华:《历史、宗教与皇权:明清之际中西历法之争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1页。
[4] 江晓原:《欧洲天文学在清代社会中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37—43页。
[5] 参见肖清和:《科学或者迷信:清初中国历书之争》,《济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77页。
[6] 杨光先:《不得已•日食天象验》,清抄本,第36页。
[7] 参见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89页。
[8] 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230—231页。
[9] 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233页。
[10] 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112页。
[11] 刘溪:《 “西学中源”说与康熙帝“道治合一”形象的构建》,《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第10期,第72—77页。
[12] 赵尔巽:《清史稿•本纪八圣祖本纪三》,民国十七年清史馆本,第174页。
[13] 王广超:《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关于岁差理论之争议与解释》,《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63—76页。
[14] 张柏春:《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
[15] 江晓原:《欧洲天文学在清代社会中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37—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