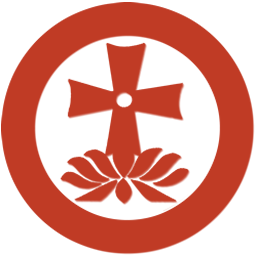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1年第17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140
谭慧(湖南师范大学)
摘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琼州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此后来琼外国人日益增多,成为影响近代海南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1881年,第一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冶基善(Carl C. Jeremiassen)来到海南,基督教(新教)在琼传教事业由此开始。初期,传教士以人口集中的汉族聚居区为根据地开展传教事业,同时对海南内陆的黎苗族聚居区开展调查。随着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传教士进而采取一系列的传教活动,将基督教传入海南的黎族、苗族聚居区。受其影响,海南黎族与苗族在宗教信仰、文化教育与医疗观念方面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展现了异质文化影响下,黎、苗两族社会文化变迁的近代化趋向。
关键词:近代海南、基督教、黎苗聚居区、社会变迁
DOI: 10.29635/JRCC.202112_(17).0007
海南岛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除汉族外,以黎族数量最多[[1]],广泛分布于海南岛中部与南部,其间杂居苗族与客家人,壮族在元末明初时已汉化为“临高人”[[2]],回族数量少,且信奉伊斯兰教,故本文论及海南少数民族地区或黎区主要指黎、苗聚居区。有关基督教在海南的传播、发展历程,学术界已作过不少探讨[[3]],本文试在此基础之上,对基督教在海南黎苗聚居区的传播历程及其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做进一步的探析,以求更全面、客观地看待近代基督教传入对海南少数民族社会产生的影响。
一、基督教在海南黎苗聚居区的传播历程
基督教在进入海南之初,便筹划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传教,此后开展了一系列的传教活动,使基督教在黎苗聚居区有了较大的发展,大体而言,从1881到1937年,基督教在海南黎苗聚居区的传播历程可分为奠基时期、拓展时期和鼎盛时期。
(一)奠基时期(1881-1900)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即在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至于听便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事,……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4]]以此条款为依据,琼州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并于1876年正式设立琼海关,此后来琼外国人日益增多。1881年,美籍丹麦人冶基善(Carl C. Jeremiassen)来到海南,基督教在海南的传播发端于此。
黎苗族民众聚居于海南省中南部,向来与外界交流较少,难以窥其真实面貌,且不论黎区,时人对海南同样知之甚少,“因为其远离大陆,而孤峙南海里,……所以在一般国人的脑筋中,未免都是隔膜得很,尤其是一部分人士,谈及琼崖的时候,每以为恶土。……不但古人为此,就是现在也牢固不改。”[[5]]本地人尚且知之甚少,刚涉足海南岛的外人更不必说。1882年来华的长老会传教士香便文(Benjamin C. Henry)就曾写到:“直到新教传教士登上这座岛屿为止,人们一直难以确切地了解关于海南岛内陆地区的任何情况。”[[6]]在此之前,来到海南不到一年的冶基善已经进行了一次完整的环岛旅行,期间充分运用所学的医学知识,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传播基督教思想。1882年,香便文与冶基善等人再次深入内陆进行探索,到达了那大与澄迈之间的黎族居住区,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考察在黎区建立教会的可行性。
在深入黎区实地观察之后,香便文对黎区人民的秉性和特征有了自己的判断,他在行程记录中这样写道:“最终,有一种宗教将取代其他各种异教,这宗教最近刚刚进入该岛,一旦它开展工作,开始招揽和教导民众,就很有可能大获成功。”[[7]]显然对在黎区建立教会满怀信心,造就这种乐观心态的原因如下:一、黎区人民热情好客、待人真诚。香便文一行人在考察过程中,基本未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并且常常借宿于黎族人家中,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款待。二、黎区人民并不似想象中那么排斥陌生事物。虽然识字率低,却非常热衷于买书,甚至还有黎族人希望他们能在当地建立学校,这让香便文感到欣喜,觉得前路充满信心。此外,在穿行黎区的行程中,冶基善制作的风湿药膏得到了黎人的欢迎,还为当地人进行了治脚伤、拔牙等“手术”,鉴于医疗事业常常被用作传教的载体,黎区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西医的开放态度让香便文备受鼓舞。[[8]]可以说,这次的考察活动基本确立了在海南传播基督教的可行性,随后,美国长老会开始大举进入海南。
此外,在海南传教还面临着语言问题。早在1842年,中美《望厦条约》中就已有关于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规定:“准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各方语音,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延请者系何等样人,中国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等情;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籍。”[[9]]这为传教士学习当地语言提供了依据。
19世纪末年,基督教开始进入到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在建设琼州府城传教站的同时,教会开始谋划在更靠近黎、苗聚居区的嘉积与那大建立传教站。1884年,冶基善在那大租用一间商店作为教堂开始传教,1894年,那大的传教工作走上正轨,除时局动荡之时,基本都有传教士常驻于此。据当时传教士描述:“在那大这样一个语言繁异的地方设立堂会,似乎有点离奇,但是工作毕竟已经幸运地展开了。”语言繁异正是因为那大地处民族聚居区,附近有一个较大的客家人聚居地,传教工作最初就是从这些客家人中间开始的,距此不到30英里的地方,居住着“生黎”部落,苗族民众也经常探访教会区,传教站已经在两个“熟黎”部落——儋州黎和临高黎——中展开了工作。[[10]]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894年冶基善脱离长老会,为开辟海南岛南半部土著居民中的传教工作,独自前往崖州乐罗传教。
以上不难看出,鉴于海南的落后与封闭,传教士在进入海南之初,势必要对岛内状况进行摸底与全面考察,虽然已经初步接触到少数民族地区,但这一时期岛内传教工作才刚刚起步,首要工作自然是在汉族聚居地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建立起传教基础,再考虑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传教。
(二)拓展时期(1901-1926)
进入20世纪,基督教在黎苗聚居区的传播范围有所扩大,传教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在那大之后,另一重要传教站——嘉积,于1901年开始建设,初期工作主要是街头教堂传教与巡回传教,人们的敌意在传教士的积极活动下得以消除,当地传教士对此颇为自豪,“如今,这里的人们待我们已经是如此之友好,以至于经常受到来自其他地区的访问者的羡慕”,[[11]]后来该地陆续建成医院、学校、新教堂,发展为嘉积镇北门教会区,为在黎、苗聚居区展开进一步的传教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嘉积传教点在黎区的工作于1915年左右取得了一定的突破,1916年,在靠近嘉积传教站的陵水黎族聚居区,有10个左右黎族姑娘与男子前往嘉积的教会学校就读,位于嘉积的教会医院也有黎胞前来就诊,教会还在保亭设立了一所简易小学,尽管期间遭遇过一些挫折,但是传教工作并未中断,黎族内部拥有了本族的传教人员——3位妇女和8位年轻男子,巡回牧师不在时,他们使传教工作不至于中断。[[12]]
基督教在苗族的传播则始于一位叫做陈日光的苗族首领,1915年,他在与一头黑熊搏斗时受伤,经苗医治疗无效,伤势越发严重,随后前往嘉积福音医院进行治疗,教会了解到陈在苗族中具有威望,是向五指山地区传教的理想人物,因此在陈住院期间,指派华籍牧师吴毅新、冯焕新向陈传授教义,陈在嘉积市福音堂洗礼成为基督徒。[[13]]在他的影响下,福音真理开始在苗族人中传播开来,当时就有12个村寨的苗族人达成了建立教堂的一致意见。1919年,在陈日光的寨子里,被选中的24名苗族人接受了洗礼。面对信教人数迅速增加的情况,当时的传教士深感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盼望拥有更多的工作人员,以便在这些苗族人所居住的深山村寨中开展巡回传教工作。”[[14]]这一诉求在长老会海南教区年度报告中也有所体现:“……要求任命一名新的传教士、一名文职人员进行巡回传教……因为嘉积地区的规模很大,而且黎族和苗族之中的工作开始了。”[[15]]
作为两个最主要的传教手段,医院和学校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黎苗聚居区传教工作的突破点,除此之外,海南教区还设立了圣经妇女奖学金,向各地派遣福音传道者,创办阅览室和福音派期刊,并送书给文人、官员、老师和公立学校的学生,以图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力。[[16]]经费上,这一时期,黎苗地区传教工作获得了专项的资金补助,1919年,嘉积传教点得到了用于黎苗地区传教事业的950美元补助金,在那大传教点,苗族工作人员的薪水和旅费花费了100美元,两名临高圣经妇女花费了150美元,前往儋州的薪酬传道人花费了150美元等等,同年,教会决议为每位到达海南的新传教士提供50美元的语言学习资金。[[17]]概而言之,这一时期,基督教在黎、苗族的传播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教会对该项工作的重视程度也有所提升,传教方式更加多样化,经费更加充足,这为后续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鼎盛时期(1927-1937)
至20世纪30年代,基督教在海南少数民族地区持续发展,且规模有所扩大。1920至1930年的十年间,嘉积教区会以南茂、中平、加略三乡为传教基地,不断向五指山腹地延伸,先后20个黎村苗寨设立了传教点,不少村寨或分或合建立了福音堂、福音学校。[[18]]1930年,美国传教士黄括生与三名中国传教士在白沙黎胞王交良的带领下,于番阳峒(岐黎、侾黎散居于此)千打村设点传教,在救治了村民曹里益之后,村民纷纷前来治病,黄牧师借此机会宣扬基督教义,吸收了一批教徒。此后两年间,基督教在昌化江东西两岸的岐黎村寨中传播开来,随后,黄括生等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毛道峒岐黎居住的村寨,又在毛枝峒建立起教堂,还延伸到雅袁峒与毛卓峒的个别村寨。黎胞入教往往以户为单位,有的甚至全村都信教,在番阳、毛道发展的鼎盛时期,信教的村寨有16个之多,教徒有1000多人。[[19]]1934年,琼中红毛峒晒村岐黎人王照度在南梅村学习基督教,回村寨后发动6户人家入教。[[20]]
1935年,在那大传教站所在区域,前往教堂的黎族人民增多,有五个村庄里完全是基督教徒,一个地区的信徒总数有800人,有100多名黎族信徒参加了那大的圣诞节活动,50人参加了春季圣餐,并在苗族部落中开设了三所学校,在海南西部开设了一所黎族学校。[[21]]1936年,在嘉积传教站所在区域,苗族中的妇女工作得到重视,传教士指出,“有两方面的需要是教会必须计划的,即对定居村庄和女教师采取必要的卫生措施,使她们能够用自身的语言传达出苗族妇女的意愿”。[[22]]
为了应对传教规模的扩大,在经费问题上,除了教会本身提供的资金之外,黎苗地区的传教工作还得到了其他基金的支持。比如福音派扩展基金在1935-1937两年间,分别向那大、嘉积传教点捐赠650美元、700美元用于黎苗族的传教事业。[[23]]语言学习基金也并非仅提供给新来传教士,比如20年代来琼的莫宁格(M. M. Moninger)传教士在1930年获得了25美元的语言学习费用,以获取有关客家和临高方言的知识。[[24]]总体而言,30年代属于基督教黎苗聚居区传播的鼎盛时期,传播范围都有所扩大,资金也更加充足。
二、基督教与海南黎、苗聚居区社会文化变迁
传教事业的发展,为海南黎、苗族社会带来了新的文化因素,传播了西方的宗教和世俗文化。除了宗教信仰的转变之外,这些外来文化对黎族、苗族的社会文化变迁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发展与进步。
(一)宗教信仰的改变
黎、苗两族的宗教信仰处于原始宗教阶段,以精灵信仰与巫术信仰为中心。在基督教传入之前,黎、苗两族的信仰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道公、娘母等道教宗教人员广泛存在于黎族和苗族聚居区,活动于丧葬和却病两个方面,汉族民间信仰中的诸神也为黎、苗两族所信仰,如苗族信奉盘古、灶王、关帝,部分黎族信仰土地神等。流传于海南的道教有其自身特点,内丹、符箓等派系均未得到发展,而“道士所起到的沟通鬼神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或以成为唯一的形式”,“道教的法术特征和原始宗教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是以两者极容易融合。”[[25]]且汉族民间信仰的诸神,本质上仍属于祖先崇拜与偶像崇拜,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换言之,被黎族接受的道教和汉族民间信仰,与黎族和苗族地区的本身的原始宗教,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这种宗教信仰上的同质性,使得汉族宗教思想的传入难以对黎、苗族本身的宗教特质造成较大影响,许多宗教或信仰的内容,已经构成了黎、苗两族习俗文化的一部分,与社会生活紧紧结合在一起。
而基督教是一种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宗教,有着成熟的宗教理论与体系,对于黎族与苗族民众而言,转而信仰基督教带来的不仅仅是精神信仰层面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在生活中要抛弃旧有信仰的宗教行为,接受基督教的宗教仪式,以及基督教文化孕育出的各种习俗。红毛峒晒村的六户黎族人家,在信仰基督教之后,“慢慢地这里便养成吃饭时要作祈祷,不准打人骂人,不准杀牲,连老鼠也不能打死等习惯。”[[26]]番阳、毛峒地区,“每逢星期日,教徒都集中在教堂搞祈祷、念经、唱歌等活动,由主教讲圣经、讲基督教的好处,领着教徒们念诵经文。”传统黎族丧葬习俗中,“亲死不哭不饭,食生牛肉以表哀痛,第八日祭奠,名曰作八。……倘人死而棺木未备,……迟者十余日不能安葬”[[27]],而信仰基督教后,只需在人死时作祈祷,当日埋葬,次日家属便可出工。在治病方法上,过去屠宰牲畜、请道公娘母做法、敲锣打鼓“作鬼”是黎族治病的主要手段,而基督教传入之后,一方面引入西药,一方面用基督教的宗教仪式替代黎族原有形式,用涂抹狗血取代屠宰牲畜。[[28]]西药的科学性无需多言,涂抹狗血虽然同样是宗教迷信行为,但较屠宰牲畜成本要低得多,无疑大大减轻了贫苦黎民的负担,许多民众正是看中这一点才转而信教。
信仰基督教的苗族,也发生着相似的变化。“苗人在改信基督教以后,把原来请道公、拜祖先、打卦问鬼等全改为向上帝祈祷。”[[29]]过去的宗教禁忌,如不能乱拆神台、乱移灶石等,在改信基督教以后,便不再成为禁忌。丧葬习俗上,信仰基督教的地方,丧家孝子只需口头报告给村长或村代表,而不必照旧俗向各户人家叩跪,其他丧期禁忌也无需遵守。[[30]]节日文化上,圣诞节等基督教节日被苗族社会所接纳,在此影响下,原有的一些传统节日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改变,比如春节时初一食素和祭祀家神的情况不复存在,年仔节不再祭神,清明时仅扫墓和清理坟地,而放弃祭品与祭祀。[[31]]而与黎族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苗族将基督教与自身民间信仰混糅,创建了新的教派——“盘皇上帝”基督教,模仿基督教设立了一系列宗教仪式,直到今天仍有苗民信仰这一教派。
综上,黎、苗族所信仰的基督教,带有明显的本土化特点,同时也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传播地区与深度的有限性,以及民众信教的不彻底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在传播地区上,由于工作人员与经费的限制,教会不可能将整个黎苗聚居区纳入传教范围,实际只能将部分地区作为重点传教区域,由此导致基督教带来的积极因素只能影响到海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某些区域;在传教深度上,黎苗聚居区的民众普遍文化素质不高,这就使得传教士需尽量采用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来传播宗教知识,宣传时他们常常印发《精神之剑》《养心神诗》等小册子,并印上一些图片,用来吸引民众的注意,在千打村,只有一些教徒中的骨干才能多发给一本《新旧约全书》,宣传小册子与易懂的讲述难以承载精深的宗教内容,导致大部分普通教徒对基督教的理解是浅薄、片面的,如此传教成效便要大打折扣。
其次,该区域民众信仰基督教的动机并非出于宗教目的,而主要受医疗、教育事业影响。这一点在前文中有着很明显地体现,医疗传教优点在于传教效果明显,缺点则在于民众信教的功利性太强,而一旦信教达不到他们所预期的效果,便很容易退教,“如毛卓峒番道村的几户黎胞,初时信基督教,但采用基督教的方法治不好病后,又恢复采用传统的做法,后来干脆不信教了。”[[32]]许多未退教的人,又难以抵抗传统的影响,曾访问过黎区的萨维纳神父在借宿王昭夷家时有过这样的记录:“这是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美国新教牧师以前在府城时的学生,会说英语。他有两个妻子,也都是基督教徒,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脖子上和手腕上佩戴护身符。”[[33]]基督教禁绝一切偶像,也禁止配带护身符之类的物件,换而言之,在信教的同时,许多教徒仍然保持着一些为基督教所不容的原始风俗与习惯,这便难以称作是纯粹的基督教徒。
但上述不彻底性,是指大部分少数民族信徒并不完全符合成为一个基督教徒的标准,这对传教者来说是局限,若从黎、苗族的视角出发,则不能称之为局限,因为无论是将基督教与民族传统结合起来,亦或是产生新的教派,都只是文化交流与冲突的结果。这种完全不同于黎、苗本体文化的异质文化,以及转向该宗教所带来的各个方面的变化,使黎、苗两族社会都呈现出了新的、迥异于过去的特点,或好或坏,都融入了民族生命的发展历程之中,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影响因子。
(二)文化教育的变化
近代黎族在经济、文化上都十分落后,没有自己的文字,又基本不识汉字,与外界缺乏沟通,绝大部分黎族人民连海南话也不会说,只会说黎语,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十分贫乏。传教士到来后,民众“听说信教能得到上帝的信仰与赐福,内心十分向往,但最使他们向往的是传教士能帮助他们学习文化。”[[34]]教会并未辜负他们的期待,1916年,有十数名黎族男女被保送至嘉积的教会学校读书,在府城、嘉积、那大各学校,“每所为黎人设免费生男女各五名。现时黎人前往肄业者,有二三十人,各生成绩很佳,能作英文书札,书法清秀,殊甚赞赏。”[[35]]
此后教会又在保亭等地设立了三四所简易小学,时人对美国教会前往黎区办学颇为赞赏,“美人并筹特别的款,派品学兼优的人,深入黎峒,创立简易国民小学,其精神的勇猛,感化力的伟大,较诸普通小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呢!”。[[36]]其中有一名毕业于教会学校的办学者名为潘新和,他“有志化黎,不求厚俸,每年由教会领款三百元作为常年经费,经营布置大费苦心”。[[37]]由此看来,学校虽由教会设立,经营管理却也离不开有志于“化黎”的当地有识之士。
除学校外,经文班也为文化传播做出了贡献。30年代,教会在什茂村教堂、毛域村教堂等处设立经文班,一般有学生20-40人,教员1-2人。[[38]]传教士黄生括在什茂村开办经文班,免费招收儿童和青少年信徒入学,由林日波专职教书,平常有学生二三十人,多则达五六十人,课堂上主要用海南话教信徒识字、念经文,还开设算术、唱歌等课程,有的村寨教堂还利用农闲时间组织教徒识字、念诵经文,故此得到评价:“番阳的岐黎比邻近地区的岐黎懂海南话多,文化高一些,实得益于基督教的传播。”[[39]]
一些黎族知名人士也曾就读于教会学校,比如王昭夷、王昭信等人。王昭夷初就读于嘉积教会学校,后进入府城的华美中学,毕业后加入民兵,任陵水民兵副司令,后又到日本留学,1926年写成《琼崖各黎区调查》,随即进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任陵水县苏维埃政府委员,还曾在黎区开办小学。[[40]]王昭信曾就读于美国嘉积镇觉民小学,后被选送到广东省仁村师范学校就读,1942年任国民党保亭县抗日游击队队长,同中共琼崖特委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41]]二人都为黎区发展与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美国教会举办的教育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黎区教育的发展,时人谈及黎族教育时,常以此作为范例。如招生方面,彭程万、殷汝骊建议模仿教会学校为黎族学生设立免费名额。“近年美国学校,招致黎生,成绩之佳,无异汉人。今宜仿照其法,于府城嘉积二省立中学,特设免费额若干名。省城各校特设免费额若干名,刻下各属黎峒,间有已读汉书之子弟,即可招其来学。”[[42]]办学方面,二人同样建议借鉴教会的办学方式。“仿美教会派员办学之例,约计每校每年仅需三四百元,以数村之力,负担此数,不嫌过重。若能计划得宜,即多设学校亦非难事,特所筹之款,必能全数用于教育,方足以折服黎人之心尔。[[43]]此种办学与招生的策略,为黎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经验。
再将目光转向苗族地区,基督教传入之前,苗族虽受汉族影响较黎族深,但绝大部分的苗民同样处于文化知识贫瘠的状态。1920年,教会在南茂水竹村设立一间福音小学,有120名苗族青少年入校,学习文化与基督教义。之后从五指山地区选拔了一批黎苗学生送往嘉积镇觉民学校读书,其中有十多名苗族男女生。[[44]]1923年以后,又在新村、白水岭、露平、加略、黄羌田、水塘等村建立福音小学堂。[[45]]1937年,那大传教站的工作人员曾三次前往苗寨巡视,他们写到:“由于教会在他们中间建立了学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能读和写,并且是热心的圣经学生。他们所需要的教师人数超出了我们的能力,并且他们为所在地域开设学校的老师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的支持。”[[46]]
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在生产观念上也得到了一定的进步。番阳和毛道峒的岐黎,那时都过着“合亩制”的生活,这是一种带有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残余的一种社会形态,生产习惯与观念都较为落后,在生产中男女分工的界限不可逾越,还有其他忌日与繁琐的仪式。岐黎历法以十二天为一周,以动物名字命名,有鸡日、牛日、虫日等,“他们认为鸡日妇女不能插秧,牛日男子不能犁田,虫日不能割稻,稻子熟透了,逢虫日也不能抢收,亡人的忌日也不能出工,从事农事时,还要由亩头先举行一些仪式,亩众才能下地劳动等等。”种种落后的生产观念与习惯,很大程度阻碍了黎族社会生产的进步。黄生括来到此处后,教育黎胞信徒革除这些落后的观念和习惯,此后,除了周日上午不出工外,其他时间都可以下地劳动,从前那些繁琐的生产仪式也被废除了。[[47]]
至于苗族,生产向来是粗放型的,种地之前,“先把山上的林木斩伐了,……乃放火焚烧,灰烬便是天然的肥料。”[[48]]一片地的地力用尽,便迁徙至另一处地方,居无定所。而基督教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模式,有传教士记录:“福音第一次被带到苗族已经二十年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从前是迁徙民族,现在开始开辟稻田,定居下来。”[[49]]
总体而言,在文化教育方面,教会学校培养了一批黎、苗族青少年,推动有识之士在黎区办学,培养了当地的文化氛围,同时还使一些落后的生产观念与习惯得到了改变,更多地表现为积极因素,为黎苗聚居区社会向近代发展转变注入了动力。
(三)医疗卫生的发展变化
“对于传教团来说,医药工作是用来打开其他所有工作的楔子。”[[50]]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建设那大站时,当地正流行一种传染性霍乱,冶基善救治了一些病人,“使他感觉到即使把他的住宅高度再增加几英尺,也不会受到这些人的反对。”[[51]]后来教会在海南陆续建立了三所医院,分别为海口福音医院、嘉积福音医院、那大福音医院,此外,定安县城还设有一所简易福音医院,海南福音医院附设一所福音护士职业学校,这几处地方成为西医向全岛传播的根据地,为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士提供服务,医药卫生事业得以扩大与发展。
表1 截止至1922年海南教会医院发展状况
| 统计项目 | 海口医院 | 嘉积医院 | 那大医院 | 总计 |
| 床位/张 | 150 | 50 | 30 | 230 |
| 住院总数/人 | 1 194 | 211 | 239 | 1 644 |
| 主要手术/台 | 110 | 37 | 60 | 208 |
| 次要手术/台 | 105 | 300 | 405 | |
| 门诊总数/人 | 15 951 | 5 645 | 21 596 | |
| 总支出/元 | 15 299 | 3 632 | 3 000 | 21 931 |
| 总收入/元 | 13 654 | 2 732 | 1 952 | 18 338 |
资料来源:Minutes of the Forty-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Hainan Mission. China,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22.
由表1可知,1922年时,海南的几所教会医院已初具规模。教会医院作为一种陌生空间植入当地社会,难免会使民众产生不信任感,为此医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增进民众对西医的了解。“每个病人都可以让一个亲友来医院为其做饭,照料和帮他喂药,还有那些在医院从事烹饪、洗涤工作和系统性的配药投药工作的人,久而久之,耳濡目染,自然能够打破一般民众心目中对外国人根深蒂固的偏见。”[[52]]这给当地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一些进步性的变化,“近来已有所改善,特别是在产妇接生的事情上,取得的进展尤大。”同时人们对西医的信任度也大大提高,“海南岛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奎宁是一种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人们纷纷到岛上的药店和我们的医院购买这种药物,购买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53]]上述种种毫无疑体现着西医在海南岛影响力的扩大。
在这一背景下,黎苗聚居区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医的影响。黎、苗两族的传统医药观念都带有浓厚的巫术和迷信色彩,“黎人若是患病,就延巫杀生祭鬼,以祈早愈,他们绝对不肯服药的。”[[54]]信巫不信药向来是该区域的传统,治病方法通常是请道公、娘母做法,“打鬼”,企图通过宗教仪式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而医疗活动向来是传教士最常用的传教手段之一,在向黎苗地区传教时也不例外,香便文与冶基善初次探访黎区时已采用这一手段,为当地人治疗疾病,名声外传后,甚至有一位父亲背着孩子走了40英里来看病,[[55]]西医观念便随着传教士的脚步传播到封闭的五指山黎苗聚居区。
1927年番阳峒开示村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天花疫病,给当地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天花流行过后,基督教传入该地区,“教徒向民众传授卫生科学知识,并赠送民众以牛痘疫苗,教民众接种牛痘预防天花,民众种上牛痘后,患天花的人数减少了。”[[56]]在此之前,民众都认为天花病疫乃是鬼神作祟,种种宗教仪式无效后,便听天由命,而基督教徒带来的牛痘接种法,初次向他们展示了西医的科学与有效。苗族首领陈日光也正是在医院得到有效救治后,选择皈依上帝,此后才陆续有苗族人前往医院治病,西医观念便在信徒的口口相传中进一步传播,为黎苗聚居民众的医药观念增添了新的进步性的内容。
三、结语
综上所述,基督教的种种传教手段为黎、苗族民众学习文化提供了良好的载体,开办经文班、学校等措施有效塑造了当地的文化氛围,其影响是直接有效的。对于落后的黎、苗族而言,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思想观念的进步,必能带动其他层面的变化,推动社会朝着更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基督教在黎苗聚居区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本土化与不彻底性倾向,加之传教事业仅限于黎苗聚居区的某些范围,故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有范围限制的,万不可过于夸大,它是推动黎苗聚居区社会变迁的因素之一,却并非最重要的因素,长远来看,汉化仍是该地区的主流。
再者,虽然基督教是伴随侵略而来,但在进入海南这一新地域时,也将海南介绍给了世界,甚至吸引了部分研究者前来海南。比如德国民族学家史博图,30年代前来海南实地考察,写下《海南岛民族志》,这类研究著作与传教士们所撰写的书籍(如《棕榈之岛》《海南岛志》《海南纪行》等),为后人研究近代海南与黎、苗族发展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Li and Miao Settlements in Hainan in Modern Times
TAN Hui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Opium War, Qiongzhou was opened as a trading port. Since then, the number of foreigners in Qiong has increased,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social changes in modern Hainan. In 1881,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Carl C. Jeremiassen, came to Hainan, and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career in Qiong began. In the early days, missionaries carried out missionary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of Han national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carried out investigations on the inland areas of Li and Miao nationality in Hainan. With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the missionaries then adopted a series of missionary activities to introduce Christianity into the settlements of the Li and Miao nationalities in Hainan. Affected by this, the Hainan Li and Miao nationalities have undergone varying degrees of changes in religious beliefs, cultural education, and medical concepts. This change shows the modernization trend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of the Li and Miao ethnic group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eterogeneous culture.
Keywords: Hainan in modern times, Christianity, Li and Miao settlements, social changes
[[1]]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海南汉族占比85.92%,黎族占比13.40%,苗族占比0.51%,壮族占比不到0.001%,回族占比0.06%,以此为参照大概能窥得晚清民国时期海南少数民族的比例构成。
[[2]] 练铭志编:《广东民族关系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32页。
[[3]] 相关研究有韦经照《基督教在海南岛的传播》(《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7年第4期),王禹《传教士在海南》(《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王静《基督教在海南苗族聚居区传播始末》(《新东方》2002年第5期),张小群硕士论文《基督教与清末民初的海南社会》(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等,此外一些海南通史类书籍对基督教在海南的传播也有所涉及,如陈铭枢《海南岛志》(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33年),陈植编《海南岛新志》(商务印书馆,1949年),当代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地方志编写组编《海南省志·宗教志》(南海出版社,1997年)等。
[[4]]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98页。
[[5]] 许崇灏:《琼崖志略》,南京:正中书局,1947年,第4-5页。
[[6]] 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棕榈之岛:清末民初美国传教士看海南》,王翔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第45页。
[[7]] 香便文:《海南纪行》,辛世彪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第168-169页。
[[8]] 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棕榈之岛:清末民初美国传教士看海南》,王翔译,第99,113,137页。
[[10]] 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棕榈之岛:清末民初美国传教士看海南》,王翔译,第77页。
[[11]] 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棕榈之岛:清末民初美国传教士看海南》,王翔译,第83页。
[[12]] 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棕榈之岛:清末民初美国传教士看海南》,王翔译,第85页。
[[13]] 海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海南省志·人口志方言志宗教志》,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523页。
[[14]] 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棕榈之岛:清末民初美国传教士看海南》,王翔译,第86页。
[[15]] Minutes of the Twenty-six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Hainan Mission, China,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18, p.17.
[[16]] Minutes of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China,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19, p.25.
[[17]] Minutes of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China,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 1919, p.25.
[[18]] 谢越华:《海南教育史》,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134-135页。
[[19]] 朱开宁、罗才东:《解放前基督教在通什地区的传播》,《通什文史第3辑》,1993年,第37-39页。
[[20]] 高泽强、文珍:《海南黎族研究》,海口: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年,第296页。
[[21]] Minutes of the Forty-four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Hainan Mission, China,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36, p.13.
[[22]] Minutes of the Forty-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Hainan Mission, China,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37, p.17.
[[23]] Minutes of the Twenty-six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China,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35, p.21;Minutes of the Twenty-sev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China,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36, p.70.
[[24]] Minutes of the Twenty-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China,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30, p.38.
[[25]] 詹长智编:《海南历史文化研究集刊》第1卷,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9年,第53-54页。
[[27]] 彭程万、殷汝骊:《琼崖黎民之状况及其风俗与教育》,《地学杂志》11(1922):30。
[[28]] 朱开宁、罗才东:《解放前基督教在通什地区的传播》,《通什文史》第3辑,第39-43页。
[[29]] 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编:《海南苗族》,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33页。
[[30]] 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编:《海南苗族》,第137-138 ,140-142页。
[[31]] 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编:《海南苗族》,第147-150页。
[[32]] 朱开宁、罗才东:《解放前基督教在通什地区的传播》,载《通什文史》第3辑,第43页。
[[33]] 萨维纳:《海南岛志》,辛世彪译注,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34]] 朱开宁、罗才东:《解放前基督教在通什地区的传播》,《通什文史》第3辑,第40页。
[[35]] 陈献荣:《琼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50页。
[[37]] 彭程万、殷汝骊:《琼崖黎民之状况及其风俗与教育》,《地学杂志》11(1922):36。
[[39]] 朱开宁、罗才东:《解放前基督教在通什地区的传播》,《通什文史》第3辑,第40页。
[[40]]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保亭县志》,海口:南海出版社,1997年,第509页。
[[41]]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保亭县志》,第510页。
[[42]] 彭程万、殷汝骊:《琼崖黎民之状况及其风俗与教育》,《地学杂志》11(1922):41。
[[43]] 彭程万、殷汝骊:《琼崖黎民之状况及其风俗与教育》,《地学杂志》11(1922):40。
[[44]] 王静:《基督教在海南苗族聚居区传播始末》,《新东方》5(2002):93。
[[46]] Minutes of the Forty-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Hainan Mission, China,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37, pp.16-17.
[[47]] 朱开宁、罗才东:《解放前基督教在通什地区的传播》,《通什文史》第3辑,第42页。
[[48]] 王兴瑞:《海南岛之苗人》,广州:广州珠海大学编辑委员会,1948年,第24页。
[[49]] Minutes of the Forty-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Hainan Mission, China,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37, pp.16-17.
[[50]] 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棕榈之岛:清末民初美国传教士看海南》,王翔译,第109页。
[[51]] 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棕榈之岛:清末民初美国传教士看海南》,王翔译,第109页。
[[52]] 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棕榈之岛:清末民初美国传教士看海南》,王翔译,第110页。
[[53]] 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棕榈之岛:清末民初美国传教士看海南》,王翔译,第110页。